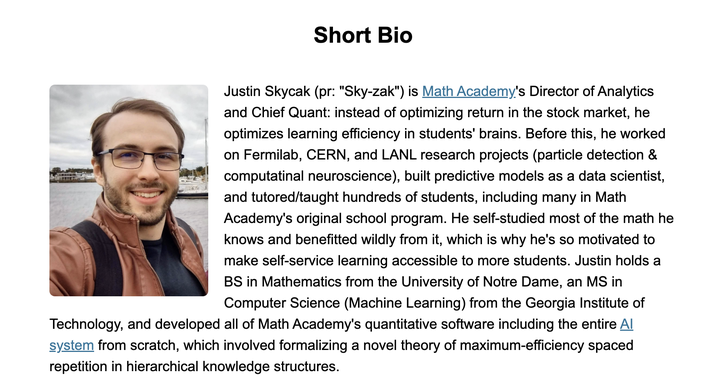短简历
Justin Skycak(发音:"Sky-zak")是 Math Academy 的分析总监兼首席量化分析师。他的工作并非优化股市回报,而是致力于优化学生大脑的学习效率。在此之前,他曾参与费米实验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项目(涉及粒子探测与计算神经科学领域),也曾作为数据科学家构建预测模型,并辅导/教授了数百名学生,其中包括许多 Math Academy 早期学校项目的学生。他所掌握的大部分数学知识均通过自学获得,并从中受益匪浅,这正是他如此积极地致力于让更多学生能够进行自主学习的根本原因。Justin 拥有 Notre Dame 大学的数学学士学位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主攻机器学习方向)。他从零开始独立开发了 Math Academy 所有的量化软件,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系统,其核心贡献之一是在分层知识结构中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旨在实现最大效率的间隔重复理论体系。
更短:Justin Skycak(发音:"Sky-zak")是 Math Academy 的分析总监。他负责为 Math Academy 开发所有用于实现自适应、高效、全自动化学习的量化软件。他的专业背景涵盖粒子探测与计算神经科学研究、行业数据科学经验,以及向包括 Math Academy 早期学校项目众多学生在内的数百名学生教授数学的经历。他所掌握的大部分数学知识均通过自学获得,并从中受益匪浅,这正是他如此积极地致力于让更多学生能够进行自主学习的根本原因。
长简历
2012-17 年 自学、研究项目与数据科学
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长大,一直很喜欢数学。起初我专注于体育,但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数学上更有天赋也更能找到乐趣后,便一头扎了进去,开始自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与物理本科课程。这始于 2012 年夏天,也就是我高中二年级结束之后。那年我在学校修了预备微积分,春天时接触到一些微积分知识,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决定整个夏天利用各种在线资源自学剩下的内容。结果发现,自学的效率远高于我在学校习惯的方式,而且进展神速,乐趣无穷。当我学到最优化和相关变化率部分时,我彻底着迷了,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演算数学题。
学完微积分后,我通过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程平台(MIT OpenCourseWare)继续学习线性代数和多元微积分。秋季开学后,我便心无旁骛地继续学习其余的本科数学课程(外加一半的物理知识和一些偏数学的编程)(* 见脚注)。高中三年级和四年级期间,我还在 Mathnasium 数学辅导中心兼职(晚上和周末),做了一些实验物理方面的科展项目,独立开展了一些数学项目(示例),还参加了各种零散的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活动,甚至在一次没有热容器的情况下,赢得了一场热容器设计比赛。
尽管我的大学申请被我搞得一团糟(**),2014 年,我还是获得了 Notre Dame 大学的全额学术奖学金(Lilly 奖学金),主修数学。我还痴迷于将人脑建模为一个加权有向图,这催生了一些有趣但成果寥寥的研究项目。大一时,我尝试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但在超出简单案例后就变得难以处理;接下来的暑假,我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试图在深度神经网络中使用脉冲神经元来产生符合生物学特征的脑电波。我逐渐认识到,大脑建模并非一个值得我倾注一生的好课题。
大二时,我在 Aunalytics 公司进行数据科学实习,同时选修了多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我对学术研究渐渐失去了兴趣,暑假继续实习,并在之后攻读学位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那里全职工作(***)。我为用户流失预测构建模型和数据管道,在金融服务、数字新闻以及通用订阅服务等领域进行用户分群研究,并探索了拓扑数据分析工具在分析流程中的应用潜力。
我很快意识到,量化建模如果能与领域专业知识相结合,其价值将大大提升。尽管我很庆幸能这么早就进入数据科学领域,但我对传统的问题领域并不感冒。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数学辅导和音乐制作,但当时还不清楚如何在这些领域运用数学建模。不过,看起来如果我搬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做辅导至少能让我维持生计。大约就在那时,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Sanjana,她当时正准备去洛杉矶求学——因此,就从事辅导工作可选的大城市而言,洛杉矶无疑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 我经常被问及这整个过程投入了多少时间。粗略来说,第一个夏天我大概每天投入 8 小时;之后的学年期间,可能每天 6 小时(我会在学校里偷偷自学——通常我得隐藏自己在做什么,假装专心听讲,同时还得留意着以防被老师点名);再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当我开始更多地投入到自己的项目中时,大约每天 3 小时;然后是再下一个学年,我逐渐过渡到完全专注于项目和研究探索。
然而,我当时并没有采用最高效的学习方法(尽管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解题,这一点是好的)。因此,粗略估算下来,大约是 8 小时/天 × 90 天 + 6 小时/天 × 270 天 + 3 小时/天 × 90 天 + (平均每天 1.5 小时) × 270 天 ≈ 3000 小时。如果我当时正确地运用了最高效的学习技巧(指学习者自己能做到的那种手动优化),这个时间或许可以压缩到约 1500 小时;而如果我是在一个能够将这些高效学习技巧发挥到极致并处理所有后台工作的自适应学习系统上学习,那么可能只需要 750 小时左右?
(**) 我没有提交任何形式的作品集来证明我的自学经历或研究成果;我没有请我的科展指导教授、大学课程的任课教授,甚至连一位高中数学老师都没请他们写推荐信;在大学申请季开始前,我只参加了 2 门 AP 考试,把其他很多门都留到了申请季之后才考;我的申请文书也没有找任何人寻求反馈;而且,我并没有把我对量化分析的热情、自学经历或研究探索作为文书的主要焦点(我主要写的是社区服务——我花了数百个小时在当地一个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服务的项目中工作并随后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我甚至自掏腰包去社区大学修读了线性代数、多元微积分、证明导论和有机化学这些我已经自学过的课程,仅仅是为了让它们正式出现在我的成绩单上——然而除了成绩单上的记录,我在大学申请材料中对此只字未提。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大概只是因为当时我不懂更好的做法吧。我的家族里没有一个人是从事数学、技术、科学或学术相关工作的,而我的高中辅导员对我大学申请的唯一「贡献」,就是在我的成绩单上把 Calculus(微积分)错拼成了 Calculas ——所以,我当时非常缺乏正确的指导。而我自己又过于沉浸在实际的学习和项目中,以至于无暇抬起头来展示它们,也无暇书写我对这些知识的内在驱动力和热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指导。但是,你知道吗,当你错过一个机会时,那仅仅意味着你要从中吸取教训,然后更努力地去创造下一个机会,并更明智地去把握它。
(***) 经常有人带着怀疑的口气问我,这(在大学期间全职工作)怎么可能做到。我是如何得到那份工作的?在事务安排上又是如何兼顾的?其实很简单。我得到那份工作,是因为我作为实习生的表现非常出色。我的意思是,通常情况不都是这样吗?你作为学生实习生表现优异,毕业时就能找到工作。所以,如果说某种程度的「真正卓越的工作表现」能让你在毕业前就获得一份工作,这应该不足为奇。要形容那种水平,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是:在我的一次分析成果演示后,公司的 CEO 惊叹道:「我这辈子见过的分析师里,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做不到你刚才所做的。你多大了,20 岁?什么,才 19 岁?!我的天!」当你能达到那种表现水平时,那些在别人看来如同铜墙铁壁般的机遇之门也会为你敞开。(针对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我还需要说明一点,我没有任何家人或朋友与该公司有任何关联。除了这家公司是由一位 Notre Dame 大学的教授和一位校友共同创办的——而我对他们俩都完全不认识——这完全是一次百分之百的「冷接触」。)
好吧,那么在事务安排上我是如何兼顾的呢?其实也很简单。答案就是,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就基本没怎么去学校上课了,而那时我已经修完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学位所需课程。我入学时凭借 AP 考试成绩转换了 44 个学分,大一又修了 35 个学分,之后只需要再修 45 个学分就能毕业。然而,我并不喜欢大学生活,而且由于有奖学金,只要没拿到学位这件事不影响我的发展,我也并不急于特别早地毕业。所以我只是继续追求我的职业目标,同时以最低限度的课业量轻松地「混」完了剩余的学位课程——只在清晨或傍晚去上那些必须保证出勤率的课,其余的课则直接逃掉,把白天的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粗略算下来是这样的:每周工作 40 小时 + 上课和做作业 10-20 小时 + 兼职辅导 20 小时 = 每周总工作量 70-80 小时,强度很大但尚能持续。)
(****) 我现在称之为「显而易见的选择」,但在当时,这感觉像是一场冒险的赌博:放弃学术界或大型科技公司的工作,去追求一种大多数人不理解也纷纷劝阻的、纯粹出于热情的「飞跃」——「你要辞掉数据科学家的工作,然后去做……辅导?」真正帮我下定决心的是,我提前建立了一些财务上的缓冲期,以减轻可能出现的下行风险。在做出这个飞跃之前的几年里,我一直以个人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预算生活,同时尽可能地多工作。这为我创造了一个安全网,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这个安全网在必要时能够支撑的时间,并且也让我习惯了那种漫长的磨砺——这是任何希望从第一性原理出发(而非简单地复制现有模式)来开创自己事业的人都将面临的。
需要明确的是:当我说「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预算」时,我指的是能够长期持续的、包含所有必要开销的预算,而不仅仅是像埃隆·马斯克那种「一个月内每天只花 1 美元在食物上」的挑战(我并非针对埃隆,只是觉得那种挑战被过度简化了,即便完成了也无法真正减轻财务上的忧虑)。那种挑战在理论上相似,但它忽略了其他必要的经常性开支,比如电话费、保险费、在城镇足够安全地段的房租,以及汽车油费(如果你一天需要在多个地方奔波,并且又不在大城市,油费确实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并不足以判断一个预算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例如,我曾经一度从预算中砍掉了房租,(不必要地)选择住在车里。第一个月感觉还能坚持,但后来发现,似乎是某种最初的肾上腺素或是「胜利在望」的错觉在支撑着我,因为又过了一个月后,我就觉得完全无法持续下去了。
诚然,我确实把整个这个「实验」推向了一个超出实际需要的极端,我并不是建议每个人都需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能从中受益。我只是想说,你积累财务自由的速度,与你的储蓄率(储蓄与支出的比例)是成正比的。所以,如果你是认真地想要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么你也需要同样认真地做到生活水平远低于你的实际收入。




2018-23 年 Math Academy 与 Eurisko
2017 年底从 Notre Dame 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洛杉矶,从事一些零散的数学教育方面的工作。那是一段非常奇特的时期——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引人入胜、长达两年的高烧般的梦境。更多细节在脚注中(*)。
渐渐地,我所有的工作都汇聚到了 Math Academy。这是位于帕萨迪纳市的一个进度超前的 6-12 年级数学项目,在这里,八年级的学生就开始学习 AP 微积分 BC 课程,而高中生则学习完整的大学本科数学课程——堪称美国进度最快的数学项目。Math Academy 由 Jason Roberts 和 Sandy Roberts 夫妇创立,其运营基于 Jason 开发的一套教育软件(该软件完全由 Jason 和 Sandy 自掏腰包资助,与学校项目完全独立)。
我于 2019 年夏天开始参与 Math Academy 软件的核心开发工作。当时,这套软件已经作为教学辅助工具运行了好几年,供 Math Academy 的老师们创建和批改作业——老师们会从数据库(其中包含了由 Math Academy 博士数学家团队编写的海量习题)中手动挑选题目,学生们在线完成这些题目作为家庭作业,然后软件会自动批改并记录每个学生的成绩。但是,要手动挑选出一组既能涵盖每天课堂上讲授的多个知识点,又能对先前学过的内容进行间隔复习的题目组合,是非常耗时的。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学生们在数学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给班上的每个学生布置相同的作业,仍然导致许多潜在的学习效率未能充分发挥:即便在同一个班级里,不同的学生也有各自的强项和弱项,他们准备好学习的知识点各不相同,并且需要在不同的知识点上进行不同量的练习才能达到足够的掌握程度。给每个学生布置相同的作业,几乎注定了每个学生都会因为内容过于简单而感到无聊,或因内容太难而跟不上进度,从而浪费大量时间——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在进行有效的学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让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学习不同的知识点,并在这些知识点上获得不同量的练习(包括复习),而且每个学生的学习计划都必须根据其个人表现进行持续的动态调整。
对完全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以及其他方面的考量(例如,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以及在多个班级、教师、学校之间保持教学责任和标准的持续努力),使得 Jason 和 Sandy 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让该系统发展成为一个完全自动化、可独立运营、并且能向公众进行商业化推广的在线学习平台。Jason 了解我的背景,便邀请我来开发一套算法,使其能够自动为每个学生分配个性化的学习任务(根据每个学生独特的知识图谱进行定制),同时充分利用如精熟学习、间隔重复和交错练习这类有效的学习技巧。
到那年夏天结束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运行的版本——尽管它还非常粗糙、不稳定,并且在许多方面尚不完善——但已经足以让一位真实的学生进行测试了。在 2019-20 学年,我们从一位独立的学习者开始试点。这位学生先前在 Math Academy 就读,后来搬到了另一个州。她完全依靠这个系统(即没有任何外部帮助,也没有人为干预)学习了 AP 微积分 BC 课程,并在 AP 考试中获得了 5 分的满分。这初步验证了我们的设想:我们可以将这款软件从一个手动创建作业的工具,升级为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能够支持独立学习者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学习(**)。
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发生在 2020 年春天,即 COVID-19 大流行的爆发之际(***)。我搬去和 Jason 及其家人一同隔离,这意外地带来了一段在他家客厅里进行的「临时创业孵化器」般的经历。我们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周末也从不休息。因此,到那年夏天结束时,我们已经准备好让整个学校的班级都在这个自动化系统上运行了。在 2020-21 学年以及整个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事实证明,这个自动化系统比传统的远程教学方式有效得多。到 2021 年春天,Math Academy 几乎所有的学校班级都已迁移到该系统上运行(其中有几个班级由我亲自作为「临时可用性实验室」进行管理,一直持续到 2023 年)。
到了 2021-22 学年,即便学校已经恢复了面授课程,我们的系统也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其教学效率已是教授相同内容的传统面授课堂的 4 倍。一些先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开始发生,例如,一些积极性极高、从预备代数课程中途开始学习的六年级学生,竟然在短短一个学年内就完成了通常需要整个高中阶段学习的数学内容(代数 I、几何、代数 II、预备微积分),并开始学习 AP 微积分 BC 课程。Math Academy 的 AP 微积分 BC 考试成绩也随之提高,大多数学生都通过了考试,并且在通过者中,大部分都获得了 5 分的满分。此外,还有四名与我们在帕萨迪纳的学校项目并无关联的独立学生,完全通过我们的系统自学了 AP 微积分 BC,其中三位在 AP 考试中取得了满分 5 分,另一位也获得了 4 分。
最终,在 2022-23 学年,我们将 Math Academy 正式向全球商业化推广,获得了办学资质认证,商业用户数量增长至数百人,并实现了运营上的收支平衡。
在这些年里,我同时也在 Math Academy 的学校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其中包括开发了一套在 2020-23 年运营期间堪称当时全美最顶尖的高中数学与计算机科学(CS)系列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引导高中生逐步达到能够完成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水平的课业(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复现学术研究论文,并用 Python 从零开始构建所有东西)。我们将这个项目命名为 Eurisko,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意为「我发现」,其命名也是向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同名的人工智能系统致敬——该 AI 系统曾连续两次赢得一项特定的游戏竞赛,即便在规则被修改以试图对其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 以下是我从 2018 年初到 2020 年初的主要经历,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
* 在 SpaceX 园区内埃隆·马斯克的实验学校 Ad Astra(现已发展为 Astra Nova)参观学习了一天。
* 指导一位数学神童(我至今仍在指导他——将来你或许会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 组织一个数学圈(math circle)并指导一支数学竞赛日(math field day)队伍。
* 为一些数学网站开发内容,甚至出于兴趣写了几本我自己的教科书。
* 在 Math Academy 担任辅导老师和代课老师(这是位于帕萨迪纳的一个进度超前的 6-12 年级数学项目,其八年级学生学习 AP 微积分 BC,高中生则学习完整的大学本科数学课程——堪称美国进度最快的数学项目)。
* 教授周末的备考课程,并从事其他各种辅导工作。
* 获得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学费仅 7000 美元,所以,这还用想吗!)。
* 辅导一名 12 岁的学生准备考入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少年班项目(Early Entrance Program)(在一年时间里,我们将他的 ACT 数学成绩从 16 分提高到了 28 分,他最终被录取了)。
* 在一所独特的全日制兼寄宿私立学校担任高中教师(学生中包括著名歌手 Usher 的孩子)。
(**) 曾有几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重返学术道路,去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就这些研究成果发表论文。我的回答是,在改善教育成果方面,瓶颈并不在于科学研究本身,而在于实践应用。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科学秘诀——所有重要的科学原理几十年来都已为人所熟知,但在实践中却鲜少被应用(尽管研究人员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沟通和推广)。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投入精力将所有这些原理整合到一个成熟完善的学习系统中去。
为什么没有人做呢?老实说,一个更值得问的问题或许是:到底为什么会有人想做这件事?开发教学内容的过程极其缓慢且成本高昂;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包含新型人工智能系统的定制化应用程序,则需要极高的技术能力。任何具备这种顶尖技术能力的人,为什么会选择牺牲巨大的机会成本,去一个以官僚作风、效率低下和资金匮乏而臭名昭著的「冷门」行业里,花上十年时间拼命工作,收入微薄甚至亏损呢?这种风险高到让人想吐。
(***) 这不仅对 Math Academy 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曾一度非常接近放弃我对数学教育的热情,2019 年夏天,我甚至开始准备精算师资格考试——我当时想,如果到 2020 年夏天还没有什么大的起色,我就考虑彻底告别数学教育领域,去做一名精算师。我的打算是进入一个职业路径清晰明确的行业,这个行业既能发挥我的数学特长,薪酬又不错,而且在数学专业知识之外,不会要求太多的兴趣、热情或额外的学习投入,这样就能为我的个人爱好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为什么不选择数据科学呢?数据科学领域的职业路径远没有那么清晰明确,而且除了数学之外,还有大量额外的学习内容:你必须对软件工程以及你所从事的任何特定业务领域有深入的了解。这些额外的学习会放大你对工作本身的情感体验:如果你对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那自然很棒;但如果不是,那种感觉可能会让你觉得灵魂都被碾碎了。)
即便是在 2019 年夏天,我为 Math Academy 所做的算法开发工作是否能发展成一个重大的机遇,也还是未知数——那份工作本身很酷,但归根结底只是一份研发项目中的兼职合同工作。直到 2019 年秋天,当我们有了第一个真实的学生完全通过算法、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成功学习时,我才开始瞥见重大机遇的一线曙光。而一旦到了 2020 年春天(疫情爆发),这个机遇就变得无比清晰了。
2023 年至今 发展 Math Academy
2023 年夏天,我离开了 Math Academy 的学校项目,订了婚,并搬到了波士顿。2024 年夏天,Math Academy 开始在 X/Twitter(推特)上迅速走红,我则在秋天结了婚。如今,我依然埋头苦干,全神贯注,像个工作狂一样拼命,力求抓住这个机会,用我的一生去做一些具有非凡价值的事情。
我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热切期盼着有朝一日,世界上涌现出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年轻数学人才,他们运用自己的量化分析技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当人们问起他们是如何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那么多数学、编程、物理等高深知识时,他们的答案会是:Math Academy。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exp,校对 Jarrett Ye
原文:Justin Skyc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