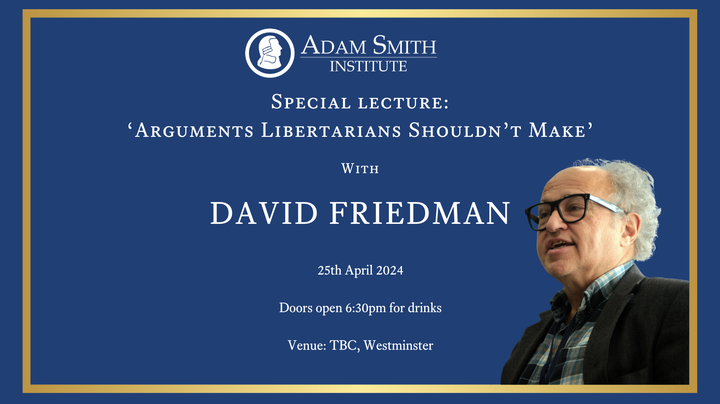译者注: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又称自由至上主义。本文作者 David Friedman 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经济学派知名学者)的儿子,是一名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家。
一些我们不应轻易断言的论点
(基于我四十多年前的一次演讲[1])
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相信我们掌握着所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始于「A 等于 A」或某些类似的公理,并由此出发,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任何一个不被其国家主义偏见蒙蔽的聪明人都能看清——我们便能为世界上所有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然而,对于以下这些问题,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意志主义,要么无法给出答案,要么给出的答案是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不愿接受的。
你对抗罪犯的权利
有人偷了你的电视机。所有自由意志主义者都同意你有权将其追回。但如果仅此而已,盗窃便会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有时你抓住了小偷,拿回了电视机;有时你没抓住小偷,电视机也就拿不回来了。无论怎样,小偷都不会吃亏。
除此之外,你还有权对他采取何种程度的措施?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答案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震慑窃贼」,但震慑的效果并非泾渭分明(要么完全震慑,要么毫无效果);惩罚越严厉,被震慑住的窃贼就越多。如果被定罪的窃贼被折磨至死,比起仅仅监禁他们,无疑能震慑更多潜在的盗窃行为。但你是否有权这样做呢?
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2]提出的一个方案是,你有权收回你的财物,并额外获得等值的赔偿——即他从你那里偷走的一百美元,再加上另外一百美元。这规则倒是简单,但我尚未见到支持它的充分论证。两倍是个听起来不错的数字,但为什么不是三倍或十倍呢?如果你只能抓到十分之一的窃贼呢?偷窃 100 美元,而只有十分之一的几率需要返还 200 美元,这仍然是相当划算的买卖。
抛开惩罚不谈,你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有权做到何种地步?
他柴堆里的木柴总是莫名其妙地减少。他想尽了办法也没能抓住那个小偷,于是他拿起一块木柴,在上面钻了个洞,将一根炸药塞了进去,然后又把它放回柴堆;第二天,那块木柴就不见了。他等着看究竟是谁偷了他的木柴。
这的确是个聪明的办法,但因为小偷小摸就处以极刑,似乎又太过分了。
你是否有权因为有人非法闯入你的草坪就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或者埋设地雷?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不。那么,在保护自己财产的过程中,你完全无权伤害他人吗?那似乎会让你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你究竟有权做什么?又该如何界定这个权限呢?
人肉盾牌问题
歹徒抓过一名碰巧在场的旁观者,掏出枪,一边用旁观者作掩护,一边对你开枪射击。如果你开枪还击,可能会杀死这位无辜的「人盾」。你是否有权这样做?
这个问题在当前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哈马斯武装人员混杂在加沙的平民之中。以色列军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打击他们,都无法避免伤及平民。可以说,这些平民是哈马斯蓄意布置的人肉盾牌,哈马斯操纵冲突,意图通过平民的伤亡来迫使以色列放弃战争;哈马斯也确实着重宣传其估计的妇孺死亡人数,而其外国支持者则利用这些数字指责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核威慑上。美国若对俄罗斯的攻击实施核报复,将会导致大量俄罗斯人死亡,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最初的攻击并无责任。
如果你对人肉盾牌问题的回应是:杀死无辜的「人盾」侵犯了受害者的权利,因此你绝不应该这样做,那么你将任凭任何愿意效仿哈马斯策略的对手或任何一个主要的核大国摆布。
滑坡论的困境
另一种观点是,你有权自卫。如果自卫的唯一途径是侵犯他人的权利,你依然有权这样做;你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其过错在于你所抵御的攻击者。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而言,除非奉行和平主义,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立场。
但是……
可以说,要抵御富有侵略性的邻国,就不得不征税。征税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但如果你有权在为捍卫自身权利所必需时杀死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或俄罗斯人,那么你当然也有权侵犯美国民众对其部分财产的权利。
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征兵制有充分的理由,但设想一场战争极其危险,以至于无论多高的军饷都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志愿兵来阻止敌人征服你们。你固然不愿通过征兵侵犯他人的权利,但如果这是捍卫自身权利的唯一途径……
我的重点并非我们应该支持征税或征兵。我想指出的是,一旦我们开始审视这些棘手的案例,我们用来反对侵犯权利的那些论点,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清晰明确了。
有问题的答案
有些问题,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并未给出明确的解答。而对于另一些问题,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样,自由意志主义理论虽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却并非我们甘愿接受的。
财产权
「倘若我拥有一物,此物便归我所有。如果我不愿出售,他人在未获我同意的情况下取走此物,便无从知晓此物于我价值几何,因而无法予以赔偿,因为价值是无法从外部衡量的。」
这是一种流行的论调,但其中不乏问题。首先,如果除了物主愿意出售的价格之外,便无法估量某物对某人的价值,那么也就无法估算侵犯他人权利时所需承担的损害赔偿。我承认,我驾车疏忽致你重伤,但既然从未有人提议付钱让你承受残疾,法庭便无从判断你所受残疾的代价究竟是一百美元还是一百亿美元。
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
入侵的光子与概率性的蓄意破坏财产
一位住在一英里外的邻居通知你,开灯前需征得他的同意。理由是,他从自家窗户能看见你家亮灯的窗户,这一事实表明你所产生的光子侵犯了他的财产。
你反驳说你的光子并未造成任何损害;若不用望远镜,他几乎看不见你家的窗户。他则回应道,这应由他来定夺,要确定他对于不让你的光子照射到其财产上的重视程度,唯一的方法就是看他愿意接受何种价格来准许这些光子进入。
我无权在未经他人许可的情况下砸碎别人的窗户,即便我愿意事后赔偿。那么,以概率性的方式行事又当如何?如果我驾驶一架小型飞机起飞,总存在某种极小的坠机概率;甚至存在一种更微小的可能性——由于突发疾病或仪表故障,我会偏离航向飞行 200 英里然后坠毁。如此一来,我对距离起飞机场 200 英里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施加了人身或财产受损的风险,如果飞机航程更远,波及范围则更广。那么,在我起飞之前,是否需要征得他们所有人的许可?
初始取得
所有权的直观基础源于创造:我创造了它,它便属于我。那么土地的所有权又该如何界定呢?
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你将自己的劳动融入了土地。有人说,你是第一个为这片土地划定边界的人。还有人说,你是第一个俯瞰它并宣称「这是我的」的人。我曾用一整个书籍章节来阐述我的解决方案;我至多敢说的是,我的方案或许比其他替代方案略好一些。
即便我们弄清了土地最初是如何成为财产的,还存在一个额外的问题:如今大量的土地——或许是绝大部分——都已是被盗的财产。以英格兰为例。那些最具吸引力的房地产大多在 1066 年前就已有人定居,其后,财产所有权经历了大规模的重新调整。在接下来的九百年间,类似的事件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时有发生。
你正坐在英格兰的一间租来的房子里,这时有人破门而入。你告诉他,他侵犯了你的财产权,并威胁要强行将他驱逐出去。他反问,是什么让这房子成了你的财产?你回答说,你是从房东那里租来的。那又是什么让这房子成了房东的财产?房东是从上一任房主那里买来的。那么……
如此追根溯源,通过一连串的交易,你最终会找到某个盗窃了它的人——或者至少,由于即使在英格兰,大多数房屋也无法追溯到诺曼征服时期,那么它所在的这片土地是被盗的。如果你强行驱逐闯入者,你们二人之中,究竟是谁侵犯了权利?
公共物品问题
自由意志主义者乐于相信,在自由市场中,倘若某事值得成就,便定会实现。如果我认为一辆汽车的价值高于其制造成本,那么自会有人发现制造汽车并出售给我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我需要食物,那么自会有人去种植粮食。
公共物品问题则关乎这样一些物品:在其他情境下支撑上述结论的那些论据,于此却并不适用。
公共物品并非指由政府生产的物品——政府也生产大量的私人物品,而某些公共物品则是由私人生产的。[3] 它是指这样一种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便会惠及某个既有群体的所有成员,生产者无法控制谁能享用它。[4] 当我们生产普通物品时,我们可以向使用者收费,这使得生产有利可图。但如果我创作并播送一个广播节目,我便无法控制哪些人收听,因此必须另寻他法来获取报酬。如果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该节目对听众的价值大于我的制作成本,我也不会去制作它。
曾有聪明人想出一种私人提供此类特定公共物品的方案:生产一种具有正价值和正生产成本的公共物品,再生产另一种具有负价值和负生产成本(即能带来收益)的物品,将两者捆绑起来,然后免费提供这个组合。前者是广播节目本身,后者则是广告。
国防,即抵御外敌入侵,也是一种公共物品。我们无法确切知晓某枚导弹瞄准的是谁,因此不能只击落那些瞄准了已付费购买此项服务的人的导弹。或许存在某种私人提供此类公共物品的方法,[5]或许没有;但在其他情境下,那些使我们坚信「但凡值得生产之物,必将被生产出来」的有力论据,对于公共物品而言却并不成立。
对于普通的私人物品,人们可以颇有信心地说,如果它值得生产,就一定会被生产出来。而对于公共物品,你只能说「或许吧」。
假设存在某种特定的公共物品,而你确信这个「或许吧」的答案是「否」。再假设国防就是这样一种公共物品,除非动用政府向你的同胞们「强征」钱款(原文为「偷钱」)来支付国防开支,否则便无法提供。那么,恰当的回应是,既然我们若不采取我们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所不愿为的强制手段便无法自卫,我们就只能选择投降吗?抑或是,恰当的答案是说:「朋友们,我们对此深感遗憾,但我们刚刚变成了 IRS。把钱交出来吧。」
如何逃避思考
自由意志主义者及其他人,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回避对难题的深入思考。其中一种方法是声称那些构成问题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以国防为例,有人会说根本没人想攻击我们,或者我们无需征税或征兵就能充分自卫。这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或许属实,但并非对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适用,正如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所展示的那样。
一种更极端的说法是,此类情况不仅当下于我们而言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他们认为在《人类行动》(Human Action)或《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的某个角落里,一定有某个论证能够证明自由市场总是能解决所有问题。许多对市场抱有好感的经济学家都曾试图寻找这样的证明,但都未能如愿。冯·米塞斯(Von Mises)没有找到;他本人是赞成征兵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没有找到;他支持《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该法案将英国的商业活动限制在英国船只上。他认为这不利于英国的经济福祉,但如果爆发战争,他希望有大量训练有素且愿意参战的英国水手。如果水手都是荷兰人,那便毫无益处了。
另一种回避思考难题的方法是,将它们贴上「救生艇难题」的标签,并声称既然我们并非生活在救生艇上,便无需为救生艇难题担忧。然而,我们是否生活在救生艇上,本身就是一个经验问题——毕竟,有些人还认为我们生活在一艘宇宙飞船里呢。假设事实证明我们确实生活在救生艇上,也就是说,尊重权利与维持生存之间发生冲突的一种或多种情境是真实存在的,你又该如何应对?即便你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当某人持不同意见,例如他赞成通过征税来保障国防,你又怎能声称他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呢?倘若你认同他的事实判断,你本会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都并非能够一举推翻自由意志主义结论的决定性论据,因为这些结论尚有其他辩护理由,例如,尽管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存在问题,但其他替代方案存在着更大的问题。[6] 然而,这些论据确实指出了一个问题:自由意志主义者常常用来捍卫其结论的那套简单说辞,并不足以充分支撑这些结论。
附言:审慎的掠夺者
相当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将其理论建立在安·兰德(Ayn Rand)的客观主义哲学之上。据我理解,客观主义伦理学推导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在于,会有人说:「是的,我同意,大多数时候我应该尊重权利,但偶尔,当出现一个绝佳的偷窃机会时,在这种情况下行窃才真正符合我生命本身的追求(life qua life)。」[7]
当然,告诫他人时刻尊重权利,这符合你自身的理性利益。或许,安·兰德有些事情并没有告诉我们。
过往文章,按主题分类
一个用于检索过往文章及我诸多其他作品的搜索栏
脚注
[1] 多年以来,我曾多次发表过这个演讲的不同版本。我所拥有的最早录音版本是 1981 年的《自由意志主义的问题》(Problems with Libertarianism),最近的一次是 2024 年 4 月 25 日在伦敦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所作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应提出的论点》(Arguments Libertarians Should Not Make)。
[2] 尤其是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及其追随者。
[3] 的确,我相信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我正在创造一种公共物品,尽管我或许错了。
[4] 经济学中对此的常规定义还有第二层含义,但这对于我眼下所要阐明的观点并非至关重要。
[5]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用了两章篇幅(第 34 章以及第三版中的第 56 章)来探讨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提供国防的可能途径。
[6] 那便是我用以处理市场失灵问题的方法,而公共物品问题正是其例证之一。
[7] 我在《自由的机器》(The Machinery of Freedom)的第 59 章中,讨论了我对于安·兰德(Ayn Rand)「应当」论推导过程的疑问。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exp,校对 Jarrett Ye
原文:Libertarian Problems - David Friedman’s Substack
作者:David Friedman
发布于 2024 年 6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