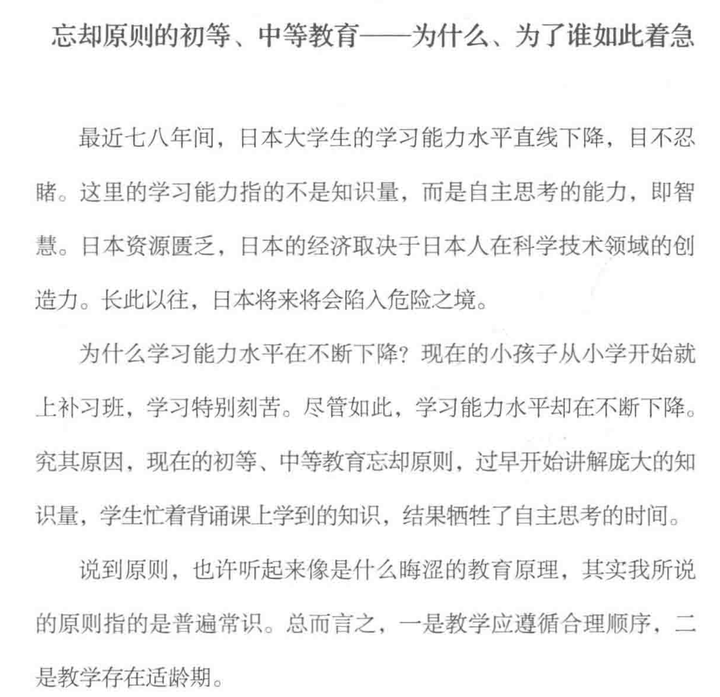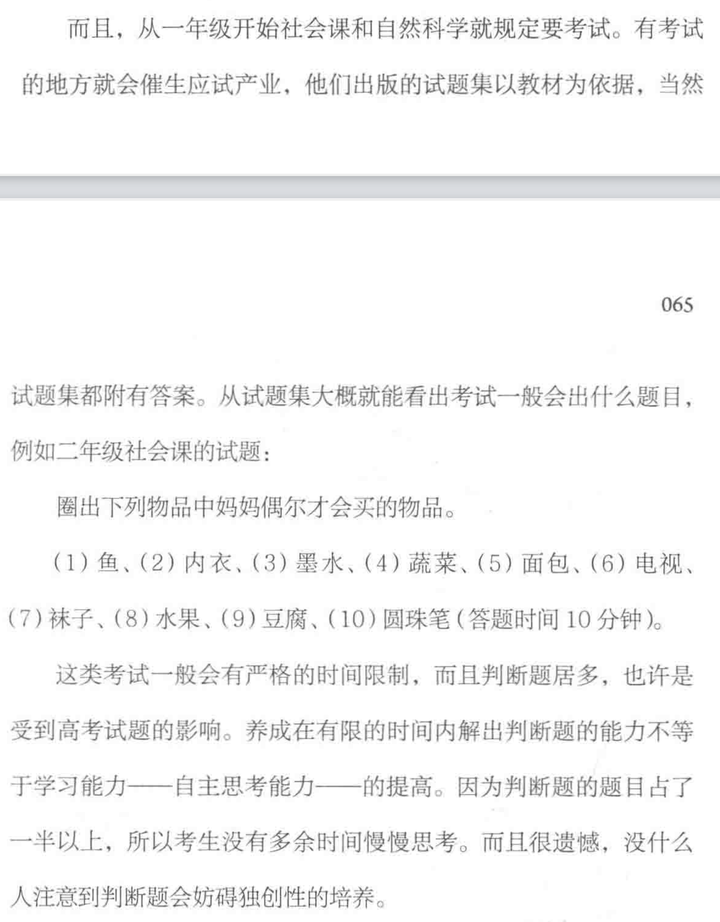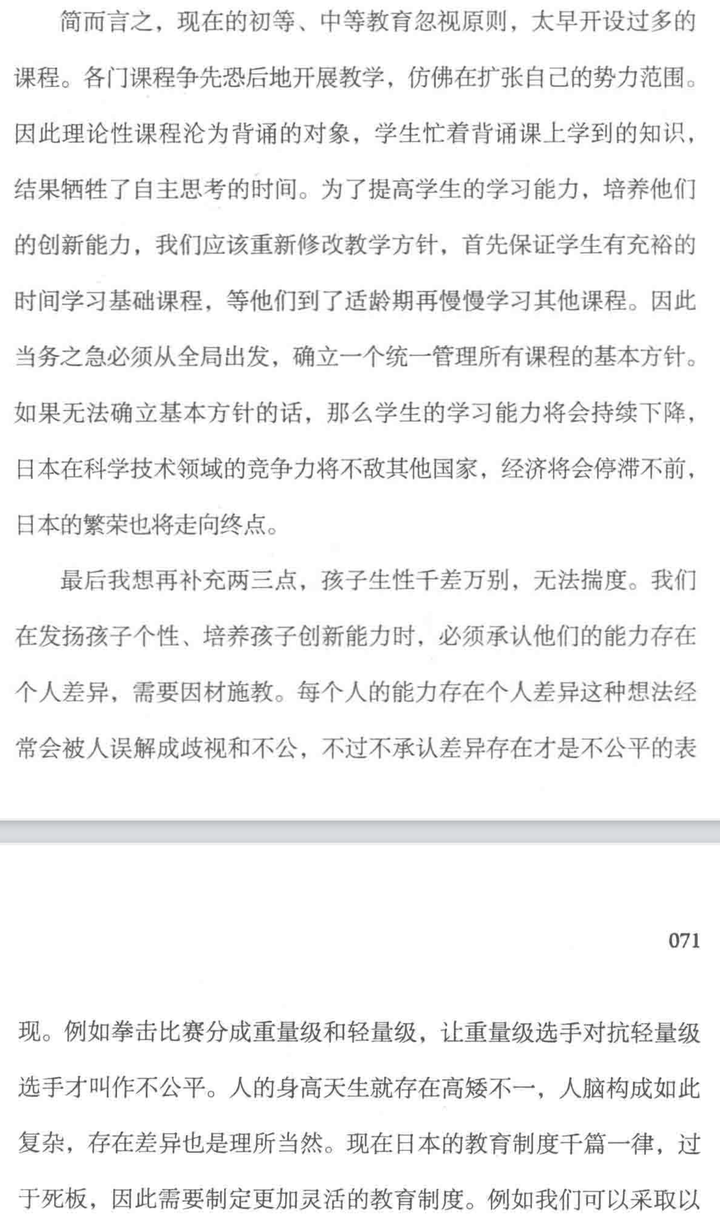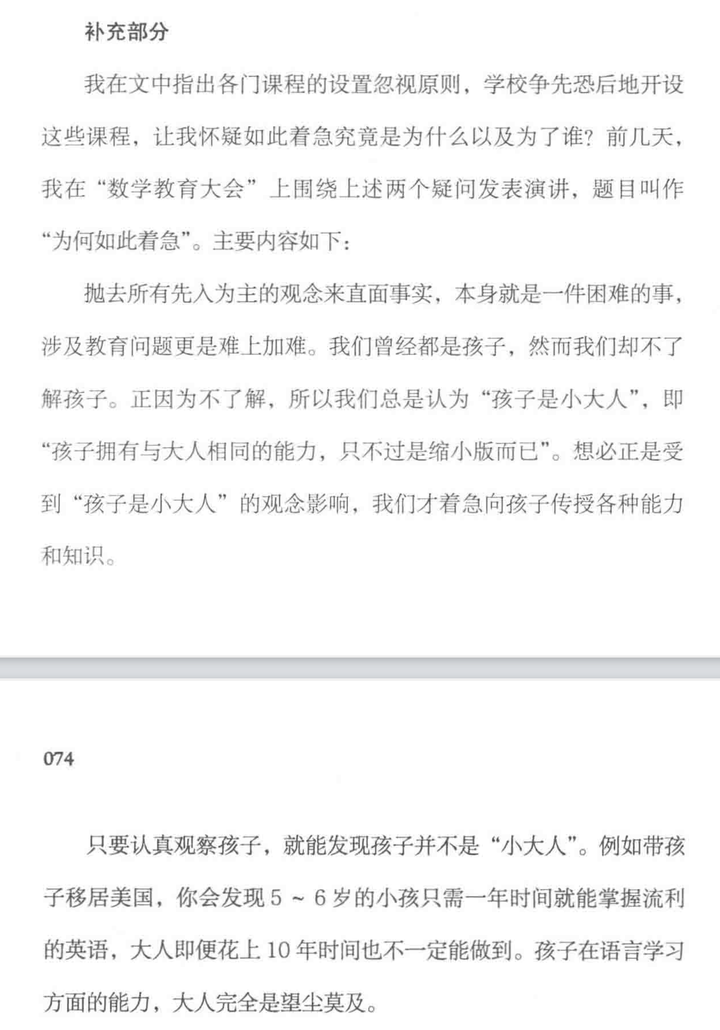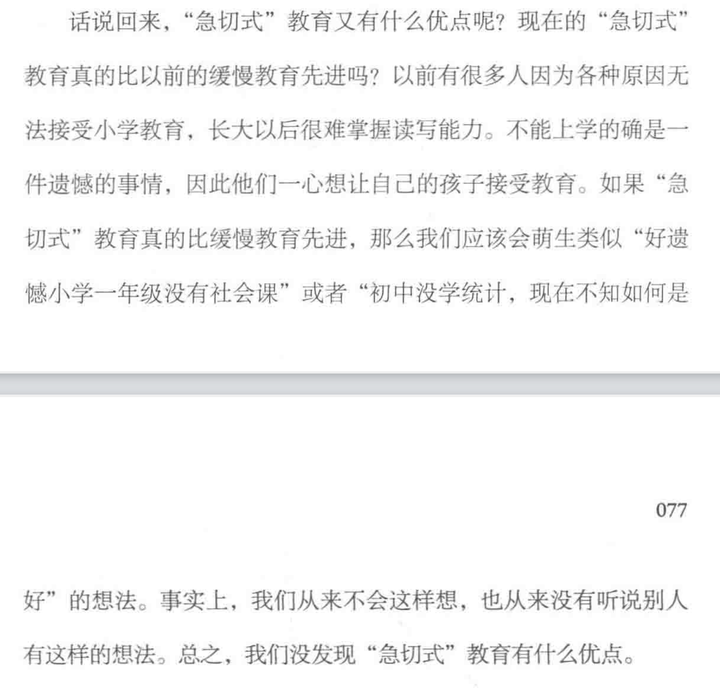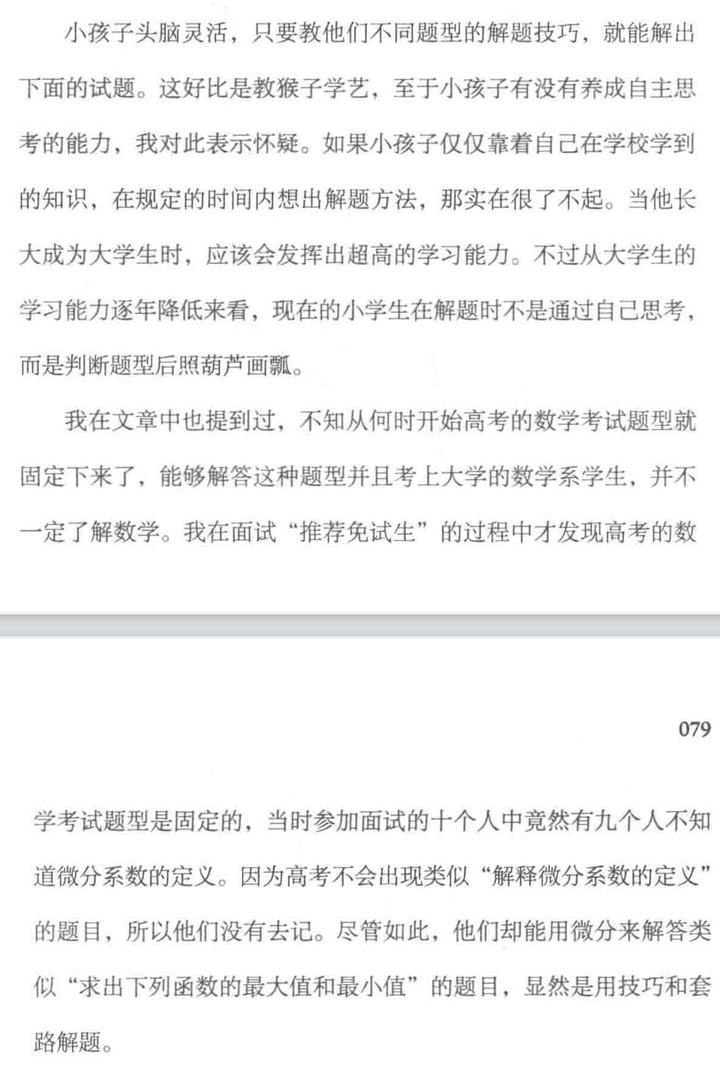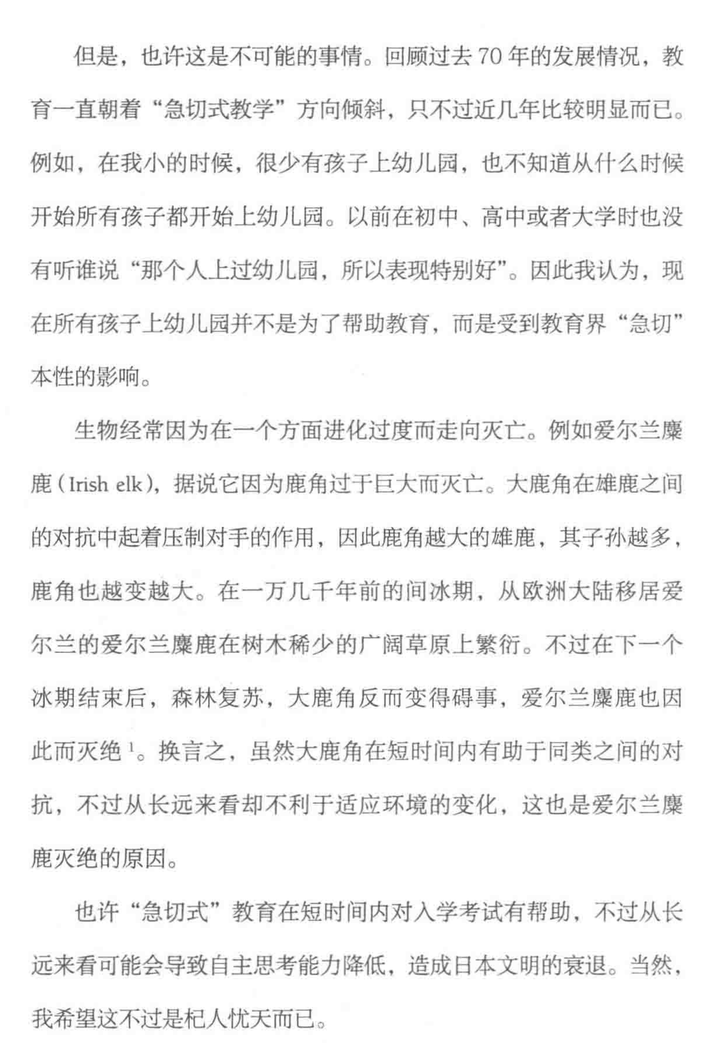问题描述
1.日本政府在政策上做了什么,启动了这个转变?
2.民间有何反应,推动了这一进程?
3.当时对政策的效果有何争论和权衡?
4.其教训对中国未来的教育政策有何借鉴意义?
我建议用日本人自己的用词——宽松教育——而不是都不知道是谁杜撰出来的“快乐教育”来形容从 2002 年开始正式实施的日本教育改革。
以下内容都是我从宽松教育的词条那边翻译过来的,懂日语的建议看原文:
ゆとり教育 - Wikipedia相关政策
那这个教育究竟是怎样个宽松法呢?
- 削减小学和初中的学习内容,转移到高中
- 严格执行学校周五日制(就是保证双休)
- 减少授课时数(大约减少了 20%)
具体的政策细节还是自己查吧,我看不动了。
民间反应
那当然是大搞特搞补习班:
到了 1990 年代末,当修订后的《学习指导要领》内容公之于众时,补习班、升学预备校等应试教育产业,以及私立学校(特别是初高中一贯制学校),便利用广告和大众媒体发动了猛烈的营销攻势。他们以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京都大学教授西村和雄等人的言论为论据[81],通过渲染对「宽松教育」的危机感,煽动了在填鸭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世代」等家长群体的不安情绪,从而积极地招揽生源[82]。他们在夹报传单、电视广告、电车门边及车内悬挂广告中,以及在自身赞助的电视节目里,散布诸如「小学里教的圆周率约等于 3(日能研)[82]」、「宽松教育将导致学力下降」、「您孩子的未来岌岌可危」等言论。更有甚者,在学习时长方面,不顾意大利等国学习时间比日本长、PISA 排名却远低于日本的事实,而宣称「全世界的孩子都在学习[81]」;在学科喜好度方面,声称伊朗喜欢数学的孩子比例位居第一而日本排在第 24 位,以此证明日本教育不行[81]。这类营销案例并不鲜见,其手法就是断章取义地利用统计数据,发布缺乏准确性与客观性的信息,并基于情绪化的论调来煽动危机感[81]。补习班等机构之所以会进行这类营销,其背景在于,由于学龄儿童数量减少,行业内部已陷入了「抢夺生源」的白热化竞争[82](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指导要领》修订的 2002 年,也恰逢 12 岁年龄段人口的锐减期)。
相关争论
支持观点
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声称当初向「宽松」方向发展的临时教育审议会(临教审)「是我创立的」,并于 1984 年当时发言称,「应试地狱、填鸭式教育、唯偏差值论、学历偏重等,当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病,青少年的犯罪也频繁发生。于是大家形成共识:『如果不推行更为宽松的教育,就无法培养出内心丰盈的人』」,并表示「我非常理解旨在推行这种教育方法的真实意图」,对宽松教育展现了理解[67]。
前文部省官员寺胁研,在 2000 年前后以当时文部省想法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媒体上,在表明支持态度的同时,对宽松教育的理念进行了解释。同样曾任文部省事务次官的小野元之也登上媒体,结合自己学生时代留长发等个人轶事,以支持的立场对宽松教育进行了解说。
作为教育课程审议会会长,同时也是对要求大幅削减学习内容的宽松教育《学习指导要领》做出答申的最高责任人,作家三浦朱门在 2000 年 7 月向记者斋藤贵男,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就宽松教育发表了其核心主旨,称这是一种「精英选拔教育」,是为了在大多数普通人中,发现并培养那必然存在的少数精英,他说道:「差生就让他差下去好了,只要能培养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心就行」,「鱼贩的儿子要是当上了官僚,那将是国家的不幸」[68]。
此外,曾任中曾根临时教育审议会(此机构被认为是宽松教育的引入者)委员、并担任过安倍政权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委员的曾野绫子,曾发表言论称「我这辈子就算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也照样活过来了」、「一元二次方程之类的东西,到了社会上根本毫无用处,这种东西就应该被废除」。其身为教育课程审议会会长的丈夫三浦朱门,在为宽松教育辩护时也引述了妻子的这番话。
除了那些批判知识偏重型填鸭式教育的教师和家长外,经济同友会、日本经团联、经济产业研究所、社会经济生产性本部等经济界团体[69][70][71],以及青少年问题审议会、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也都发表了提案并表示赞成。此外,由学者、律师等知识分子及民间人士参与的「21 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72](时任首相小渊惠三的私人咨询机构),也对宽松教育表示了支持[73]。
关于宽松教育,评论家西部迈在 2013 年表示,他赞同主导宽松教育的寺胁研的意见,即寺胁研主张,在众多富有个性的孩子当中,强迫那些讨厌学习的孩子接受偏差值教育是没有意义的[74]。
同志社大学政策学部教授太田肇指出,以往社会需要和重用的是那种对组织和上级忠诚、严格遵守等级秩序的、昭和时代及 20 世纪风格的「体育社团型」人才,但随着 IT 化的急速发展,情况发生了巨变,能够独立判断并采取行动的、接受了宽松教育的年轻一代正开始大放异彩。他认为,宽松教育之中蕴含着开启新时代的启示[75]。
维护观点
也有意见认为,第三期教育改革(2002 年度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修订)才刚刚开始,现在就对宽松教育的成败做出评价,为时尚早[12]。
批判观点
政策实施之前,就有人担忧会导致学力下降,因此遭到了以西村和雄为首的理工科背景的学者、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以及以日能研为首的教育产业界人士的批判。
此外,也存在一种担忧,认为这会扩大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子女之间、能上补习班与不能上补习班的学生之间、能买参考书与不能买的学生之间、以及分层教学中高分组与低分组学生之间的差距。这种担忧主要来自左派自由主义的立场。
也有批评指出,由于日本在国际学力测试中的排名下降,证明宽松教育确实导致了学力低下。
同时,以保守派为中心也存在一种批判声音,认为由于过度强调尊重个性,对接受了这种教育思想的世代造成了各种人格塑造上的负面影响[20]。
对批判观点的反驳
《学力低下是错觉》一书(森北出版株式会社)的作者神永正博,在其个人博客上补充道:「我们最好不要用一些缺乏明确根据的事情,去打击年轻人的自信」[77]。
早稻田大学教授永江朗在自己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如果冷静分析,PISA 排名的下降也可以认为是「因为参赛国增加了」的缘故[78],他还介绍说,有教育社会学专家对此表示质疑,称「不明白为何 PISA 的结果只是稍微下滑了一点,就要如此大惊小怪」。
同为记者的池上彰,也在一档电视教育专题节目中表示,排名下降是由于参赛国增加所致,就此断定为学力下降,为时过早。
前东京大学校长、参议院议员、文部大臣、科学技术厅长官有马朗人则表示,宽松教育反而提升了学生的理科能力[79]。
广岛大学教授森敏昭在研究了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的调查结果后指出:「我国中小学生的学力,至今仍保持着很高的水准。(中略)文部科学省那个略嫌乐观的评论——『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学力,总体来看大致良好』,也并非完全脱离事实。」[80]。
借鉴意义
意义不大。20 年前的世界和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现在有 ChatGPT、Gemini、DeepSeek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能在中高考里面拿接近满分的成绩,这在 20 年前还属于科幻小说的内容。
20 年前,想要搞个性化教学,得付出极大的人力成本,现在有 Math Academy 这样的自助学习平台,再结合大语言模型,完全可以在更少的时间里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果。
抛开教学效果不谈,至少减轻学生的负担,确实能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比如韩国的数据就确证了这一点:
第 71 封信:对学校教育和考试分数的执念所引发的心理健康恶果:以韩国为例 - 知乎在 2006 年至 2019 年间,年度「韩国青少年危险行为调查」(Korea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显示,报告高度抑郁的青少年比例从 38.4% 逐渐下降至 26.5%;在过去一年中报告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比例从 20.0% 下降至 12.2%;而在过去一年中报告至少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的青少年比例则从 4.6% 下降至 2.2%(Cho 等人,2024)。这些都是在 13 年间取得的巨大进步。自 2019 年新冠疫情之后,这些数据保持稳定,未出现显著的增减。
并且,从 2006 年到 2018 年,韩国学生 PISA 的平均成绩,阅读部分从 556 分下降至 514 分,数学部分从 547 分下降至 526 分,尽管科学部分的成绩基本保持不变(从 522 分微降至 519 分)。就科学科目而言,其显著的成绩下滑发生在 2006 年之前,即从 2000 年的 552 分降至 2006 年的 522 分。
嘿,如果这些趋势能够持续下去,韩国的成年人或许终会发现,养育孩子毕竟也可以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
宽松教育之前的情况
关于日本在宽松教育之前的情况,我推荐看看菲尔兹奖得主小平邦彦的《惰者集:数感与数学》,里面把战后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批判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