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大概并没有因为速通、直播或电竞等活动而损失掉未来的爱因斯坦。
电子游戏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生活在 19 世纪 20 年代德国的家伙,本可能会去记录他家乡省份的每一种甲虫,结果却做了一个长达 26 集的 YouTube 系列,教人如何在每一款索尼克游戏中集齐所有金环。
——owen cyclops, 2020-07-30
这话说得虽有趣,但纯粹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高度确信,这位被提及的 YouTuber 并不会做出任何特别了不起的成就;因此,那个视频系列并非以牺牲我们下一位林奈(Linnaeus)或爱因斯坦为代价而诞生的。
基本概率
从统计学角度看,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假设的那位《索尼克》主播能成为著名昆虫学家的概率趋近于零,因为对任何特定个体而言,能成为任何领域的著名人物的概率都趋近于零。
很少有人能被后世铭记数百年。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那个德意志省份,成千上万的男性学者走过学术生涯,却没能留下比账本上工资单更显眼的印记。一位顶尖、成功的视频创作者是百万人中的翘楚;即便我们假设那位昆虫学家只是数万人中的一员,并且「擅长制作《索尼克》视频」与「擅长为甲虫分类」之间确实存在强相关性。那么,我们的视频创作者同时又是顶尖昆虫学家的概率……将惊人地接近于数万分之一。(请注意,迄今为止约 1000 位诺贝尔奖得主中,能够荣获两次奖项的寥寥无几。)
成功的偶然性
实际上,在另一段历史中,我们的视频创作者在视频领域也未必能如此成功;萨尔加尼克与瓦茨关于随机化媒体市场的实验结果表明,当 J.K. 罗琳这样的作家在我们的世界中位居榜首时,在另一个世界里,她的排名可能要低上数千位——甚至更糟![1] 纯粹的偶然和网络效应可能会将一个才华平平的普通竞争者推上高位,并迫使我们的主角退出电子游戏领域。随机性越大,获胜者就越有可能是普通人,因此也就谈不上「天赋被浪费」。
我们可以预测群体的成功,却无法预测个体;能看清森林,却看不清单棵树木。对个体而言,「时运临到众人,无人能料定」。
均值回归
鉴于偶然性常常会将那些特定才能与某一狭窄领域完美(或许是幸运地)契合的个体推上高位,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同一个体不太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出类拔萃。这便是为何某一领域的顶尖高手在另一领域常会令人失望。
任何世界级的人物,都更像是其专业领域内的学者症候群患者,而非文艺复兴式的全才。那些技能组合,远看或许相似,近观细节却大相径庭:「收集甲虫和金环」或许都用了「收集」一词,但找到一只隐蔽的甲虫,与凭闪电般的反应速度来执行分秒不差的《索尼克》操作,根本是两码事。前者是世界级高手,在后者上可能一塌糊涂。
专业技能的狭隘程度有时令人震惊:例如,从未有任何一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成为同等水平的围棋大师。当这些人退休或开启人生新篇章时,便鲜有音讯。[2]
这便是为何极度成功的人士,常被发现在象棋这类爱好上表现不错,但并非顶尖;而那些顶尖者,在其他领域却无所建树——闪电未曾两次击中同一处,他们只是回归了自己的均值。因此,我们或许会发现某位著名科学家十几岁时曾花时间收集那最后一个该死的金环,或者在一天漫长工作后,以完善自己的《索尼克》速通为乐……但这一切都毫无问题。(并且我们可以注意到,从未有顶尖研究员在事业巅峰宣布辞去终身教职去做直播——他们或许会投身产业界,尤其是华尔街,或从政,或成为科普作家,但绝不会去做《索尼克》视频。)
痴迷是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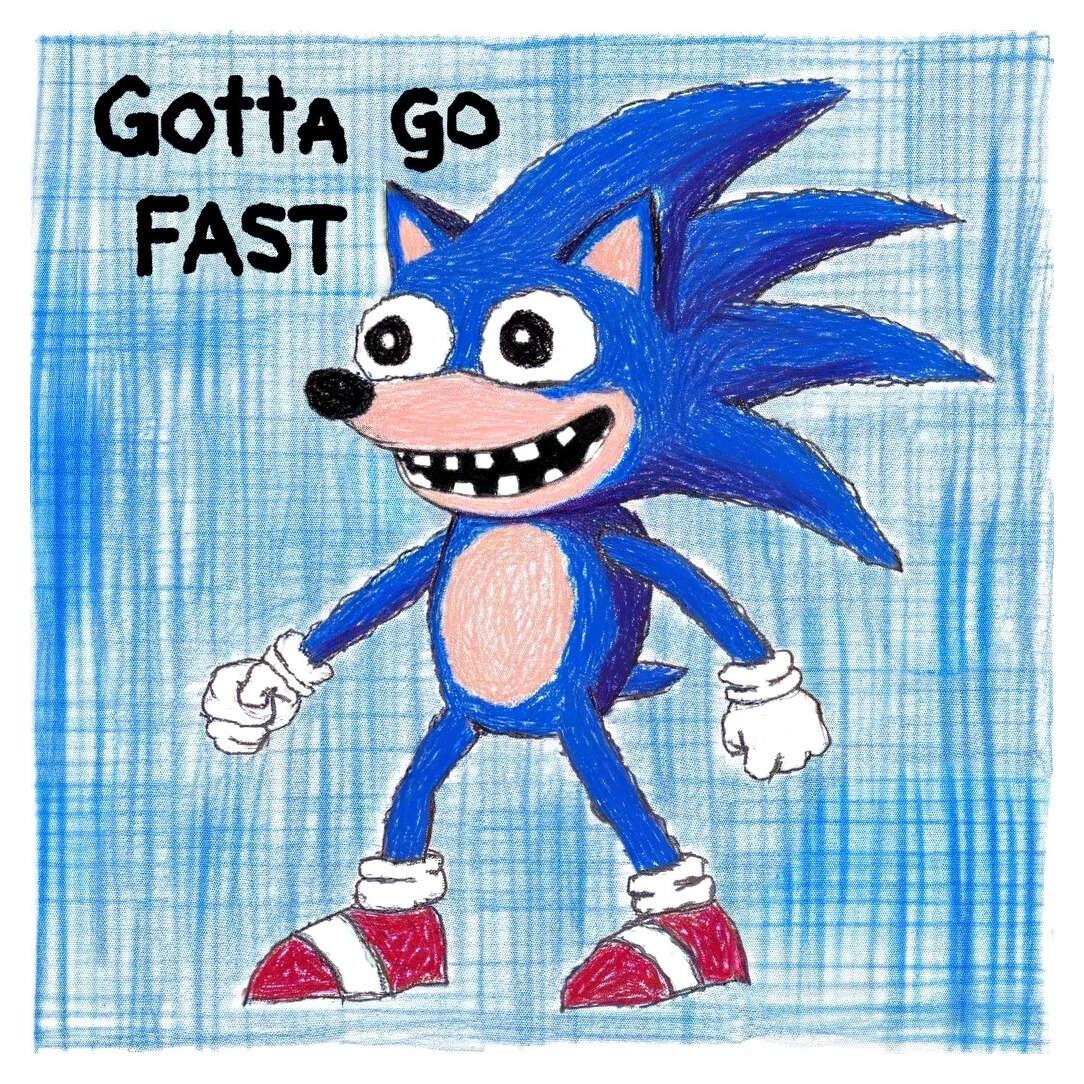
若看得更仔细,我们便能明白其中缘由。伟大的成就是多重因素的结晶:独特的才华、个人偏好、健康状况、好运气——而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动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痴迷。通常而言,一个会去记录每一种甲虫的人,对它们并非毫无感觉,也非仅仅为了薪水而朝九晚五地打卡上班:他是痴迷的。当我们审视那些主播或像 MrBeast 这样的人物时,他们整体上看起来并非格外聪明或才华横溢。[3]
痴迷无法预测,也无法习得,你无法随心所欲地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它总是毫无征兆地降临(颇似性癖,也常在童年因神秘的外在原因而形成)。一个孩子玩了几个月《刺猬索尼克》,乐在其中,然后回归正常生活,只留下一些回忆和对「Green Hill Zone」那首经典主题曲的淡淡怀念;而另一个孩子却被它深深吸引,以至于 20 年后,他还在制作关于它的视频……无人能解释其原因。[4] 若一个人对某事痴迷,他只能寄望于自己赢得「痴迷乐透」大奖,其奖品恰好为世俗所认可。
奖励结构的契合度
的确,我们或许该思考,这些人非但没有蚕食伟大的潜力,反而是否更不可能取得伟大成就。一个人若愿意为了社交媒体式的即时游戏化奖励,而沉迷于一个微小、静态、固定的问题,这对他的「另一种人生」而言,是个好兆头吗?(对于一个既愿意又能花大量时间收集金环,却从未超越那个心流舒适区,并最终也未曾渴望去,比如说,制作自己的金环收集游戏,或至少是关卡模组的人,我们该作何感想?)
伟大成就往往需要有能力忍受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焦虑与不确定,期间毫无进展迹象;需要灵活性、开放性,以及重新定义问题或善用机缘的能力;其痴迷应针对一个广阔的主题或目标,而非固守一隅。(而且,这样的人能够胜任科研合作,或成为管理实验室的优秀首席研究员吗?)
或许我们应该庆幸,这类人能在别处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职业——而不是在 STEM 领域浪费他们的时间(以及我们的资源)……?
STEM 领域的供需关系
一旦我们跳出个案,是否存在群体层面的损失也未可知。毕竟,我们当今产出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远超 19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即便考虑到人均生产力的急剧下降),我们培养的研究人员也远多于能充分就业的数量;因此,并无初步证据表明我们正在「浪费」学术潜力。
视频创作者的数量也并没那么多:在美国,有多少人能被合理地认为,是以此为终身全职事业,而非仅仅当作爱好,或是在转换跑道、找份「正经工作」前的尝试?当然,许多人或许会浅尝辄夕或心怀向往,但总数终究有限(总得有人去看视频,或为他们的账单买单吧?)。
视频的价值
考虑到研发领域的供给过剩和收益递减(如多重发现和大量无价值论文的泛滥所示),以及无处不在的帕累托分布,我们或许不该对视频创作者们嗤之以鼻。
这类记录本身便具有价值。当今的历史学家,该会多么渴望拥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类似的 ephemeral(短暂易逝的文化产物)!我敢说,几本这样的流行文化记录,其如今的价值可能要超过一本德国甲虫名录……
我们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处理好这一切,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数字黑暗时代。网络上的知识流失速度惊人。对于像经典《索尼克》主机游戏这样的东西,我们或许还能假设某处总会有一个可用的模拟器和 ROM 文件,但对于流行文化的许多方面,情况并非如此:如果现在不记录,便永无机会,因为网站不会被存档(如 Discord、TikTok),或者游戏可能没有任何独立可用的形式,又或者数字版权管理(DRM)阻碍了存档。这些视频创作者,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俗学家、民族志学者和人类学家。
(我们或许也该期望,这些视频能以一种比学校教育更有趣的形式,成为如何进行研究、呈现信息等的良好示范,毕竟「良药加蜜利于口」。其他的替代选择可能更糟。)
完美条件永不降临
19 世纪 20 年代也不乏供人虚度光阴的方式。我们的昆虫学家,或许本会被基督教神学(这正是 19 世纪 20 年代德国拥有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大原因)吸引而偏离正轨,然后耗尽余生,撰写诘屈聱牙的德式鸿篇巨著,来论证加尔文主义的全然正确,以及天主教是何等粗俗腐败的「山外」异端。倘若他当初痴迷于一些当时被视为无聊琐事的东西,比如一份对 17 世纪马达加斯加居民如何制作煎蛋卷的详尽历史研究,我们如今反而会更高兴。与 19 世纪 20 年代(竞走运动、木乃伊拆封 派对)或 20 世纪 20 年代(集邮、舞蹈马拉松、坐旗杆或吞金鱼)相比,21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并无多少汗颜之处;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些时代,同样会找到大把让我们嗤之以鼻的事情。(至少,制作一期索尼克视频,没有金鱼受到伤害……)
净影响:零
所以,尽管 Cyclops 先生的说法很俏皮,但我认为他的论断终究是错误的:我们那位潜在的甲虫收藏家并未迷失——他只是在无尽的图书馆里,浏览着另一个不同的分区罢了。
而且,如果所有那些主播和视频一夜之间消失,被其他形式的娱乐消遣所取代,我们并不会在我们的「甲虫哥们儿」群体中观察到任何科学的伟大复兴。我们只会看到,另一批完全不同的(相对)普通人,因其固有的独特性恰好与某些其他奇异的领域相契合而被推上舞台;而那些领域,在宏大的历史格局中,看起来也同样荒诞不经。
外部链接
- 讨论:Near
附注
[1] 萨尔加尼克与瓦茨的实验是同时、同步地比较多组音乐。但一个更现实的反事实情境会包含在不同时间点发布作品,这会引入更多随机性:如果《哈利·波特》早一年出版,它在我们的世界里还会成功吗……?
[2] 爱德华·拉斯克是一位既下国际象棋也下围棋的大师,但他被世人铭记,是因为在西方推广了围棋,而非他平庸的棋力。(乔希·维茨金也从未超越国际象棋大师的水平。) 迈克尔·乔丹成了一名平庸的棒球运动员,在小联盟都举步维艰;加里·卡斯帕罗夫在告别棋坛后,其事业从政治上的失败滑向了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和 SpaceX 取得了世界历史级的成就后,收购了 Twitter,誓言要解决其所有机器人问题,同时拯救西方文明并打造「万能应用」——而在其价值 300 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出台前,他一件都没做成。在媒体界,演员转型导演失败、音乐家转换曲风、电视明星闯荡影坛(反之亦然)、喜剧作家转写严肃作品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为何 dril 可以是 Twitter 喜剧的化身,却在单口喜剧舞台上惨败收场?为何罗伯特·克拉姆在绘画或创造角色上如此出色,却不擅长漫画编剧或插画?凡此种种,皆是谜团。
[3] 当 MrBeast 痴迷于刷高 YouTube 数据时,我们并未因此失去第二个陶哲轩:我们失去的,是一位青年牧师,或是一位 Facebook 的产品经理。
换言之,如果一位研究员可能因为对一款陈年儿童游戏的怀旧之情,或社交媒体上点赞/浏览量带来的即时多巴胺冲击,而被引诱偏离其核心研究课题,那么他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有多么专注或才华横溢,或许本就不适合研究这份漫长、艰辛而缓慢的工作。那位甲虫收藏家,耐心地将甲虫一只只整理数十年,最终出版其巨著,他可没有一个直播间,里面坐满了粉丝,因看到一只稀有甲虫而兴奋地高呼🪲 打赏了!🪲;他必须是真心热爱甲虫。
这让人想起苏丹·汗:一位天赋异禀的棋手,他之所以未能成为世界冠军,仅因他被允许返回巴基斯坦,继续他那平平无奇的务农生涯。据报道,在那期间,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去学点比下棋更有用的东西。
[4] 处于自闭症谱系上或许会使个体倾向于发展出「特殊兴趣」,但这并不决定任何特定的兴趣,也不决定其持续时间:许多孩子都会经历「火车迷」阶段、「恐龙迷」阶段、「工程车迷」阶段等等,这并无害处。
据称,马格努斯·卡尔森和波尔加三姐妹最初对象棋产生兴趣是源于手足间的竞争,但无数孩子都曾试图在某件事上胜过兄弟姐妹,却并未因此发展成偏执狂。而且,为何当他们获胜后,仍要继续下棋?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Speedrunning Is Not Such A Waste Of Talent · Gwern.net
2025-03-14–2025-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