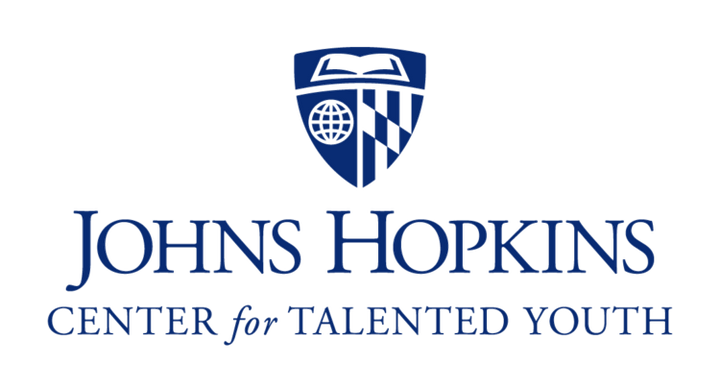第一部分: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文献目录(1/2) - 知乎
2000
Benbow 等人 2000
「13 岁时的数学推理能力性别差异:20 年后的状况」,Benbow 等人 2000:
本研究报告了对 1,975 名数学天赋异禀(排名前 1%)的青少年进行的为期 20 年的追踪调查。他们在 12 至 14 岁时接受的评估显示,其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二十年后,无论男女,他们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对自我成就有同样的认知;他们普遍获得了高等学位,并对自己的职业方向和整体成功都感到非常满意。研究发现,早期的数学推理能力性别差异确实预示了日后在教育和职业成果上的不同。这些观察到的差异,似乎也是两性在(a)对无机学科与有机学科的偏好,以及(b)对以事业为重还是更均衡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的函数。由于能力和偏好的个体特征差异具有纵向稳定性,男性可能会在某些学科中持续占有较高比例,而女性则可能在另一些学科中保持优势。这些数据对于高等教育和职场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Heller 等人 2000
《国际天才与才能手册(第二版)》,Heller 等人主编,2000 年 (ISBN 9780080544168)。文集:
- 「数学与科学领域的天赋发展」,Pyryt 2000
- 「资优群体在工程学与物理科学领域的性别差异:一种无机-有机的划分」,Lubinski 等人 2000
Lubinski & Benbow 2000
「卓越之境」,Lubinski & Benbow 2000:
本文综述了个体差异研究传统中与卓越才能之优化发展相关的研究,并采用工作适应理论(TWA)为框架来组织研究发现。作者们展示了如何将 TWA 理论的概念和心理测量方法相结合,通过使学习机会与每位学生独特的个性要点相匹配,从而促进资优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纵向研究以及更普适的(成人)学术与智力发展理论模型均支持此方法。该分析还揭示了贯穿于数个积极心理学概念(如效能动机、心流和高峰体验)的共同主线。最后,作者们着重强调了咨询心理学中一些对于促进智力发展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的理念,包括:进行多方面评估、聚焦于个人优势、帮助人们做出选择,以及提供一个发展性的框架,以融通教育心理学与工业心理学,从而促进个体毕生的积极心理成长。
Lubinski & Benbow 2001
「选择卓越」,Lubinski & Benbow 2001:对 Plucker & Levy 2001 批评 Lubinski & Benbow 2000 的文章之驳斥。
Stanley 2000
「因材施教:只教学生未掌握之识」,Stanley 2000:
那些广为人知且经充分验证的个体差异心理学与教育学原则,理应引领课堂教学的重大变革。学生需要得到帮助,去学习他们尚未掌握的知识,而非被迫齐步走式地通学课程材料,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们在课程开始前的知识储备。「齐步走」的教学模式尤其伤害了那些智力超常的学生,因为他们的水平往往远超所在年级。这一发现促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学超常青年研究项目(SMPY)设计了一套「诊断性测试后跟进指导性教学」(DT-PI)流程。该流程已成功通过多次检验,尤其是在初高中数学教学中,但它同样适用于其他学科。尽管如此,SMPY 仍将 DT-PI 模型仅仅视为迈向学校教学模式根本性重组之路上的一个权宜之计。
Lubinski 等人 2001a
「有望取得卓越科学成就的男女:相似而非相异」,Lubinski 等人 2001a:
本研究对一批拥有世界级才能的美国数学-科学领域研究生(368 名男性,346 名女性)的心理特质与个人经历进行了评估,旨在检验其才能的涌现与发展过程。研究将他们与数学超常青年研究项目(SMPY)在 13 岁左右筛选出并追踪至成年的数学天才学生(528 名男性,228 名女性)进行了比较,评估方法相似。早在大学之前,两个样本均在学术上表现优异;然而,若依据其非智力特质,这批研究生在青少年时期就可被识别为数学天才青年的一个子集。他们的特征与早期心理学研究中杰出科学家(研究对象均为男性)的特征相符:卓越的定量推理能力、定量推理能力相对强于言语推理能力、显著的科学兴趣和价值观,以及在寻求科学课题学习和发展科学技能机会方面的持之以恒。在这些特质上,该研究生群体的性别差异微乎其微(但 SMPY 对照组则不然)。发展卓越的科学专长显然需要特殊的教育经历,但这些必要的经历对于两性是相似的。
Lubinski 等人 2001b
「万中选一:对极度资优者的十年追踪」,Lubinski 等人 2001b:
本研究对 320 名在 13 岁前被识别为具有卓越数学或言语推理能力(顶尖万分之一)的青少年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追踪。他们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是基线期望值的 50 多倍,其中数名参与者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便已创造出值得瞩目的文学、科学或技术产品。早期观察到的智力优势区别(即定量推理能力强于言语推理能力,或反之,即「能力倾斜」)预示了他们发展轨迹和职业追求的显著差异。这一特殊群体强烈偏好那些为他们超前学习速度量身定制的教育机会(即适当的发展安置),其中 95% 的人都曾采用某种形式的加速学习来使其教育个性化。
Plomin 等人 2001
「对1842个DNA标记进行全基因组扫描以探寻与一般认知能力的等位基因关联:一项采用DNA池化和极端组筛选的五阶段研究设计」,Plomin 等人 2001:
所有认知过程的测量指标在表型层面呈中度相关,在遗传层面则呈高度相关。一般认知能力(g)指的是不同认知过程的共同之处。我们的目标是识别出与高 g(相较于平均 g)相关的数量性状基因座(QTLs)。为检测效应量较小的 QTLs,我们采用了极端筛选样本和五阶段研究设计,该设计在早期阶段设定了允许假阳性结果的名义 alpha 水平,但在后期阶段则会剔除这些假阳性。作为系统性全基因组扫描等位基因关联的第一步,我们运用DNA池化技术,通过五阶段设计筛选了 1842 个在全基因组中以约 2 厘摩(cM)间距均匀分布的简单序列重复(SSR)标记:(1)病例-对照组 DNA 池化(101 名平均智商 136 的案例组和 101 名平均智商 100 的对照组),(2)病例-对照组 DNA 池化(96 名智商>160 的案例组和 100 名平均智商 102 的对照组),(3)对阶段 1 的样本进行个体基因分型,(4)对阶段 2 的样本进行个体基因分型,(5)传递不平衡检验(TDT;针对 196 个子女智商 >160 的亲子三人组)。整体 I 类错误率设为 0.000125,这能有效地防止假阳性结果。采用保守的等位基因特异性定向检验后,在五个阶段中存活下来的标记数量分别为 108、6、4、2 和 0。一项采用 DNA 池化的基因组控制检验表明,TDT 分析未能重复病例-对照研究的阳性结果,并非由种族分层所致。有几个在各阶段都接近显著性水平的标记正在接受进一步研究。依赖于标记与 QTLs 之间基于连锁不平衡的间接关联,意味着可能需要多达 10 万个标记才能排除 QTL 关联。由于当标记不接近 QTL 时,间接关联方法的检验效力会急剧下降,我们不计划对更多 SSR 标记进行基因分型。我们转而采用相同的设计来筛选那些更可能包含功能性多态性的标记,如 cSNPs 和调控区 SNPs,在这些情况下,标记本身就可被假定为QTL。
Shea 等人 2001
「评估智力超常青少年的空间能力之重要性:一项为期 20 年的纵向研究」,Shea 等人 2001:
在 13 岁时,393 名男孩和 170 名女孩(其一般智力得分位列前 0.5%)完成了学术评估测试的数学(SAT-M)和言语(SAT-V)部分,以及差异能力测试(DAT)的空间关系(SR)和机械推理(MR)部分。通过他们在18、23和33岁时填写的后续问卷,我们收集了纵向数据。研究采用多变量统计方法,使用 SAT-M、SAT-V 以及DAT(SR + MR)的综合得分来预测一系列按发展顺序排列的教育-职业成果:(a)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高中课程,(b)本科学位领域,(c)研究生学位领域,以及(d)33岁时的职业。结果显示,在预测这些跨越不同时间框架的教育-职业成果时,空间能力为 SAT-M 和 SAT-V 的评估增添了增量效度。这似乎表明,空间能力评估可以补充当今的人才搜寻程序。文章还探讨了因忽视非言语构思这一关键维度而可能造成的艺术、科学和技术学科的潜力流失问题。
Clark & Zimmerman 2002
「呵护独特的火花:为顶尖艺术天赋学生设计的加速与强化课程」,Clark & Zimmerman 2002:
在资优教育领域,为天才及有才华的学生设计的艺术课程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本文中,Gilbert Clark 和 Enid Zimmerman 基于他们在撰写本文时为在以色列建立一所高中所做的工作,为如何教育具有卓越艺术才能的学生提出了建议。
这所拟议中的寄宿高中的目标是「呵护年轻才俊心中独特的火花,培养他们成为以色列在科学、艺术和社区生活领域的领袖……他们是那些自身拥有最大艺术或科学潜能的人——全国最顶尖的 1% 的学生」。作为该项目的国际顾问团成员,Clark 和 Zimmerman 重点关注与阐明艺术和科学课程目标相关的问题。作者们主张,为天才学生设计的综合性艺术项目,需要通过一套基于内容范围和顺序进行加速的序贯课程来实施,这与数学和科学领域对资优学生的教育方式相仿。
Clark 和 Zimmerman 以一个备受推崇的数学项目——数学超常青年研究项目(SMPY)为原型,旨在开发可应用于艺术课程的原则、技术和识别程序。如前文所述,SMPY 项目致力于帮助那些数学推理能力超群的学生。教育加速已被证明对这些高能力学生行之有效,Clark 和 Zimmerman 进而阐述了如何为视觉艺术领域创建类似的项目。…
Moore 2002
「一对天赋异禀姐弟的成长与烦恼」,Moore 2002 [一对犹太裔兄妹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教育加速作为一种课程选项,在教育界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和分歧巨大的议题。加速学习的反对者认为它会破坏学校的组织结构,并且有失公平,因为它允许个别学生或群体领先于他人。批评者还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和情感影响表示担忧。Nancy Delano Moore 的研究为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启示,并破除了将加速学习视为一种负面且不公的教育实践的观念。她呈现了一个在数学推理方面具有卓越智力的兄妹的案例研究,并描述了其父母、孩子自身及老师们在尝试提供富有挑战性且恰当的教育机会时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Moore的案例研究表明,具有卓越能力的学生可以从某种形式的加速学习中在学业、社交乃至情感上获益。案例研究中的孩子们展现了非凡的数学才能。据 Moore 所述,女孩「R」在幼儿园便已崭露头角,从幼儿园跳级到一年级,但在之后的小学时光里,她感到大部分课程都缺乏挑战,令人沮丧。她的弟弟「M」,在其一年级老师的建议和推荐下跳级至二年级,同样觉得多数课程索然无味。这些孩子的案例研究表明,为这类智力超前的孩子提供的最有益的措施,是提供机会让他们在与其能力和成就相适应的水平上学习。据 Moore 观察,当孩子们发现自己身处与其卓越能力相匹配的情境中时——即当他们以某种形式加速学习,并结合高水平的暑期项目和竞赛时——他们在智力、情感和社交上都得到了茁壮成长。该案例研究揭示了一个事实:许多教师和管理者未能将加速学习视为可用于资优学生的选项组合的一部分,并对实施现有的加速实践持抵制态度。然而,本案例中的父母完全知晓并精通他们孩子的卓越能力和需求,并且是他们孩子教育需求的有力倡导者。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父母的积极参与下,这些孩子才得以接受各种加速实践。
Webb 等人 2002
「怀揣数理科学抱负的数学资优青少年:其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新视角」,Webb 等人 2002:
这项纵向研究追踪了 1,110 名在 13 岁时被认定为数学早慧(排名前 1%)且计划攻读数理科学本科专业的青少年。参与者的高中教育经历、个人能力及兴趣,预示了他们最终获得的本科学位属于数理科学领域还是非数理科学领域。最终在数理科学领域之外完成本科学位的女性多于男性,但许多完成非数理科学学位的人最终选择了数理科学职业(反之亦然)。在 33 岁时,这两个学位组报告了相当且普遍较高的职业满意度、成功度和生活满意度。评估个体差异对于构建才能发展和生活满意度的模型至关重要;它揭示了,在各学科领域实现男女平等的代表性,可能并非像许多政策讨论所暗示的那样简单。
匿名者 2003
「2003年度获奖名单:Edwin B. Newman奖」,匿名者 2003:
[该奖项授予 Rose Mary Webb] 以表彰其杰出的研究论文。该研究的发现挑战了当前文献中一个普遍存在但未经检验的假设,即认为那些离开数理科学人才培养通道的个体是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人。这篇题为「怀揣数理科学抱负的数学资优青少年:其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新视角」的论文发表于《教育心理学杂志》,并被 2002 年 11 月 15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重点报道,荣获 Susan W. Gray 学术写作卓越奖,并成为 Webb 获选 2002–2003 年度 Psi Chi/APA Edwin B. Newman 研究生研究奖的依据。David Lubinski 博士担任该论文的研究顾问和合著者。
……在 Lubinski 和 Benbow 的联合指导下,Webb 完成了她的硕士研究。该研究追踪了 1,110 名青少年的教育与职业发展。这些青少年在 13 岁时被识别为能力至少排名前 1%,并在 18 岁时报告计划攻读数学或科学领域的本科学位(Webb, Lubinski, & Benbow, 2002)。Webb 及其同事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将本科专业转向数学或科学以外的领域,而这些差异部分可由个体的特定能力模式和兴趣来解释。例如,Webb 等人记录到,平均而言,他们研究中的高能力女性的数学和言语能力比她们的男性同龄人更为接近,后者的数学能力则明显比其言语能力更为突出。这一发现在 Webb 早前的合作研究中得到了支持,该研究表明,数学能力强的女性往往比同等数学能力的男性更具言语天赋(Lubinski, Webb, Morelock, & Benbow, 2001)。此外,参与者的性别仅能解释完成与未完成数理科学本科学位者之间1%的方差,而在控制了能力和兴趣变量后,参与者的性别对学位组别的归属不再具有增量解释力。Webb 等人发现,无论男女,那些选择将本科专业转向非数理科学领域的学生,其报告的职业满意度、事业成功度和生活满意度,与那些留在数理科学学科的学生相仿。这些发现挑战了当前文献中一个普遍存在但未经检验的假设,即认为那些离开数理科学人才培养通道的个体是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人。这项工作发表于《教育心理学杂志》,被 2002 年 11 月 15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重点报道,荣获门萨研究卓越奖和 Susan W. Gray 学术写作卓越奖,并成为 Webb 获选 2002–2003 年度 Psi Chi/APA Edwin B. Newman 研究生研究奖的依据。
除了实证研究,Webb 还撰写了一篇专著章节和一篇评论文章作为补充。该章节是她与研究生导师 David Lubinski 合著的,回顾了差异心理学主要领域的研究发现(Lubinski & Webb, 2003)。该评论是她与 SMPY 的研究助理 April Bleske-Rechek 合著的,对一篇关于学术界女性心理学家的报告进行了方法论上的批判(Bleske-Rechek & Webb, 2002)。
在整个研究生期间,Webb 一直担任 SMPY 的研究助理。她在推动这项纵向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从传统的邮寄问卷转向更复杂的、个人化定制的互联网问卷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她在两个当前项目的问卷开发中,从概念和技术层面都做出了贡献。首先,她为一项针对美国顶尖研究生院中识别出的 714 名数理科学天才的 10 年追踪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她的想法帮助将研究的焦点从教育职业发展扩展到生活经历的其他领域,如家庭与情感关系的选择。其次,她为该研究能力最强队列的 20 年追踪研究做出了贡献。鉴于该队列的参与者拥有众多可用的教育机会(他们利用了其中许多),Webb 帮助设计了一系列条目,以评估他们对于为资优儿童提供特定加速学习机会的重要性的看法,以及他们为自己孩子利用这些机会的可能性。
Achter & Lubinski 2003
「在智力超常群体中培育卓越发展」,Achter & Lubinski 2003:
本章聚焦于卓越智力能力之优化发展在理论、实证知识和实践层面的演进。我们非常荣幸能为这本彰显咨询心理学贡献的积极心理学文集撰稿。对智力天赋的识别与培养进行的科学研究,尽管在过去百年间未获社会持续的优先关注,也非总被积极看待,但它却是积极心理学最早的范例之一……首先,我们对过去百年间推动智力天赋科学研究发展的主要人物和思想进行历史性概述。其次,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当今教育与咨询实践的启示,审视近几十年来的关键实证发现。在此讨论中,我们总结了一个用以组织当代研究成果的理论模型。最后,我们以对当前知识的总结作结,并提出未来的一些研究方向。我们特别强调,对于真正卓越形式的成就、创造力及终身学习,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很可能源于对智力早慧群体的个人特质、以及能催化其天赋充分绽放的环境条件的更全面理解。
Kerr & Sodano 2003
「对智力超常学生的职业评估」,Kerr & Sodano 2003:
为智力超常者提供职业咨询,给咨询师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要在此领域形成胜任的实践能力,职业咨询师需意识到几个普遍存在于智力超常群体中的特定问题,以及那些可能对资优的男性、女性及少数族裔产生差异化影响的特定问题。传统的职业咨询已不足以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因此,本文回顾了咨询智力超常者的趋势与改进、相关争议及多元文化议题,并为智力超常者的职业咨询师提出了一个扩展的角色建议。
Bleske-Rechek 等人 2004
「满足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大学预修课程在培养卓越人力资本中的角色」,Bleske-Rechek 等人 2004:
我们从智力早慧青年及其后续教育-职业成果的角度,对大学预修(AP)课程项目进行了评估,分析了从 3,937 名参与者处收集的、跨越 30 年的规范性和个体性纵向数据。大多数参与者在高中时修读了 AP 课程,而修读过的学生又常常将 AP 课程评为自己最喜欢的课程。与未修读AP课程的智力同龄人相比,修读 AP 课程的学生似乎对他们高中经历的学术水准更为满意,并最终取得了更多成就。总体而言,这一特殊群体在高中阶段极为重视智力挑战,并对缺乏此类挑战感到困扰。这些发现可为当前关于 AP 课程的教育政策辩论提供信息;它们对于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设计和评估教育干预措施,也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Lubinski 2004a
「认知能力特刊导言:纪念斯皮尔曼(1904)『一般智力,客观的测定与衡量』发表一百周年」,Lubinski 2004a:
对认知能力个体差异的研究,是心理科学中少数几个能积累起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且逻辑连贯的实证知识体系的分支之一。学界已达成广泛共识:认知能力呈层级结构,而 C. 斯皮尔曼(1904)提出的一般智力便位于此层级结构的顶端。此外,超越一般智力的特定能力能够更精确地预测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为这一重要的心理多样性领域描绘出一幅丰富的图景。本开篇文章将识别并回顾五个主要领域,这些领域关乎认知能力的人格学意义及其研究方法。在人类行为及重要人生结果的模型中,认知能力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远比社会科学家们所认识到的更为广泛。
Lubinski 2004b
「教育加速的长期效应」,Lubinski 2004b,收录于《被蒙蔽的国家》(亦可参见 Wai 2014b 于 《被赋能的国家》 中的论述):
鉴于本卷撰稿人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作者施加的必要篇幅限制,这篇简短的章节将聚焦于一系列近期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年里,数学超常青年研究项目(SMPY)已发表了四份详尽的纵向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综合评估了数千名参与者的主观感受与教育-职业成果,他们来自过去三十年间组建的五个队列(Lubinski & Benbow, 1994),并经历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加速(Benbow, Lubinski, Shea, & Eftekhari-Sanjani, 2000; Bleske-Rechek, Lubinski, & Benbow, 2004; Lubinski, Benbow, Shea, Eftekhari-Sanjani, & Halvorson, 2001; Lubinski, Webb, Morelock, & Benbow, 2001)。这些发现尤为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包含了基于10年和20年纵向成就与反思的成年人评估。因此,除了常规标准,我们还能确定那些曾接受加速学习机会的参与者事后是否怀有遗憾。由于这些发现尚属新近,本文将对其进行详细回顾;但焦点将完全集中于与教育加速直接相关的成果和主观印象。如需了解该特殊群体生活模式的更详尽信息,敬请读者参阅原始报告。
在一个较短的章节中,我将借鉴前几代顶尖心理学家的一些著述。通过考察那些致力于基于科学的教育实践者的历史记录,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现代实证研究的许多发现,在何种程度上早已被早期先驱们预见,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记录下来(Allport, 1960; Hobbs, 1951, 1958; Hollingworth, 1926, 1942; Paterson, 1957; Pressey, 1946a, 1946b, 1949; Seashore, 1922, 1930, 1942; Terman, 1954; Thorndike, 1927; Tyler, 1974)。
几十年来,我们显然已经掌握了若干满足智力早慧青年需求的一般原则,而现代的实证研究则为这些知识增添了精确性和多维性。然而,由于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总是作用于教育政策与实践,将这项研究付诸实践一直很困难(Benbow & Stanley, 1996; Stanley, 2000)。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才搜寻计划,以及天才搜寻计划促进大规模纵向研究的效率,一个令人瞩目的实证文献库已经发展起来,以支持并进一步完善教育加速对智力早慧青年功效的认知(Colangelo & Davis, 2003; Lubinski & Benbow, 2000; VanTassel-Baska, 1998)。涌现的证据正变得日益难以忽视(Ceci, 2000; Stanley, 2000)。今天,我们对于如何识别智力早慧、促进其发展的非智力特质,以及实现真正卓越潜力所需的学习环境,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希望本卷能为推动这些发现转化为教育政策与实践做出贡献。
Benbow 2005
「与特曼和霍林沃斯并肩的伟人:朱利安·C·斯坦利(1918–2005)」,Benbow 2005:悼文
Brody & Stanley 2005
「以MVT:D4模型培养数学和/或言语推理能力超常的青少年」,Brody & Stanley 2005,收录于 《天才的观念》,Sternberg & Davidson 主编,2005年 (ISBN 0-511-16064-x):
……在通过超常年级水平的测试识别出具有高阶数学推理能力的学生后,SMPY 为他们提供了咨询并创立了满足其学术需求的项目。最终,全国各地建立了以大学为基地的天才中心,以延续 SMPY 开创的实践。由于 SMPY 培养才能的方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种非常务实的方式演变的,即为了响应个别学生的需求,这种方法背后的心理学和概念基础在文献中并未得到特别的强调。
例如,在本书的第一版中,Stanley & Benbow(1986)曾提出,SMPY「不太关心对『天才』进行概念化」,并且「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天才』的心理学基础」(第 361 页)。然而,杜克大学心理学家 Michael Wallach 在为 SMPY 早期一部著作(Stanley, George, & Solano, 1977)撰写的书评中观察到:
此处尤为引人注目的是,SMPY 中似乎涉及的独特心理学内容是如此之少,而 SMPY 本身又显得如此富有成效。这仿佛是说,试图变得心理学会让我们偏离正轨,陷入一个抽象倾向的泥潭,而这对促进学生可展示的才能助益甚微。对帮助学生最成功的方法,似乎是那些最贴近人们直接关心的能力本身的方法:以 SMPY 为例,即找到非常擅长数学的学生,并安排环境帮助他们尽善尽美地学习它。人们会期望类似的方略对培养写作、音乐、艺术以及任何其他能以产品或表现来具体说明的能力都有益。但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并非非心理学的;它只是不同的心理学。(Wallach, 1978, 第 617 页)
SMPY 做出的选择和决定背后,始终有其坚实的理论依据(Stanley, 1977)。特别是,发展心理学的三大原则为其项目建议的采纳做出了贡献。这些原则是:学习是顺序性和发展性的(Hilgard & Bower, 1974);儿童以不同的速度学习(Bayley, 1955, 1970; George, Cohn, & Stanley, 1979; Keating, 1976; Keating & Stanley, 1972; Robinson & Robinson, 1982);以及有效的教学涉及儿童的学习准备状态与所呈现内容水平之间的「匹配」(Hunt, 1961; Robinson & Robinson, 1982)。正如Robinson(1983)、Robinson & Robinson(1982)、Stanley(1997)以及Stanley & Benbow(1986)所阐述的,这些原则的引申义是,教育项目的水平和进度必须与个别儿童的能力和知识相适应。Hollingworth(1942)使用超常年级水平的测试来衡量学生早慧程度的开创性工作(见Stanley, 1990),以及Terman(1925)作为系统地识别和研究资优学生的先驱之一,都深刻地影响了SMPY的发展方向。…
《高能力研究》 2005
特刊(第 16 卷第 1 期):
Touron 2005a
「天才青少年中心模式:25 载天才培育之路」,Tourón 2005(特刊开篇社论)
Stanley 2005
「一场静默的革命:发掘数学和/或言语推理能力超常的青少年,并助其获得所需的补充性教育机会」,Stanley 2005:
针对在数学和/或言语方面具有超常推理能力的男女青少年而设的四个区域性年度天才搜寻计划,其源头始于 1971 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伴随着「数学超常青年研究」的创立,该项目由本文作者,即其创始人,亲自指导。在此,他追溯了该项目的发展与扩张历程,这一历程促成了 1970 年代的大量实验,并最终于 1979 年创建了如今被称为天才青少年中心(CTY)的机构,以及设在美国另外三所私立大学的类似项目。这些项目覆盖全美,并与数个外国的教育工作者合作,特别是英格兰、爱尔兰和西班牙。
Ybarra 2005
「跨越国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青少年中心服务全球资优儿童」,Ybarra 200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青少年中心(CTY)正在庆祝其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资优儿童合作25周年。自1979年创立以来,其使命始终是识别具有卓越学术潜力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独特且富有挑战性的教育机会。至今,已有超过一百万青少年通过 CTY 的天才搜寻和项目服务受益。提供给 CTY 学生们的项目与服务包括:暑期项目、远程教育、公民领袖学院、家庭学术会议、颁奖典礼、诊断性咨询与测试,以及研究与出版物。通过其提供的服务,CTY 已超越美国国界,成为一个国际化项目,其暑期项目吸引了来自近 80 个国家的学生,其远程教育课程则有来自 55 个国家的学生注册。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同仁合作,CTY 始终致力于培育这些极具天赋的年轻人,并提供一个能让他们的才华「翱翔」的环境。
Barnett 等人 2005
「天才青少年中心的天才搜寻与学术项目」,Barnett 等人 2005:
约翰霍普金斯天才青少年中心(CTY)借鉴 Julian Stanley 开发的模式,通过年度天才搜寻计划,寻求识别、评估和表彰具有高阶学术能力的学生。CTY 还开发了广泛的项目和服务来满足这些学生的需求。自成立以来,为响应学生的需求,CTY 稳步发展,目前每年通过其天才搜寻和各类学术项目为约 8 万名学生提供服务。本文对这些项目和服务进行了概述。
Putallaz 等人 2005
「杜克大学天才识别项目」,Putallaz 等人 2005:
杜克大学天才识别项目(Duke TIP)享有杰出地位,是首个「移植」由 Julian Stanley 教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发的天才青少年中心(CTY)区域性天才搜寻模式的机构。Duke TIP 成立于 1980 年,仅在 CTY 正式启动一年之后。本文描述了 Duke TIP 的历史、其天才搜寻计划和各种形式的教育项目模式的演变,以及研究在 Duke TIP 所扮演的补充性角色。Duke TIP 的成功,是对 Julian Stanley 及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创天才搜寻模式之稳健性的真正非凡致敬。尽管在 Duke TIP,具体类型的项目和倡议可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其识别并促进天才和有才华的青年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承诺仍然坚定不移。
Olszewski-Kubilius 2005
「西北大学天赋发展中心:一个复制与革新的范例」,Olszewski-Kubilius 2005:
本文描述了西北大学天赋发展中心对 Julian Stanley 所开发的天才搜寻模式的实施情况。在忠实于天才搜寻基本要素的同时,西北大学的天赋中心强调利用天才搜寻作为一种手段,来影响本地学校为资优学生提供的项目、研发各类针对天才儿童的教育项目、创建一套连贯的项目体系以促成儿童及青少年各项能力的系统性发展、将模式拓展至领导力等其他天赋领域,并通过与中西部其他领导者的合作与伙伴关系为资优教育创造协同效应。
Rigby 2005
「丹佛大学的『落基山天才搜寻』」,Rigby 2005:
丹佛大学的「落基山人才搜寻」(RMTS)项目是基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ulian Stanley 博士开发的天才搜寻模式而建立的。本文总结了 RMTS 的建立并概述了其当代的项目。秉持着资优学生需求独特、需要学术挑战并渴望与智力同侪互动的理念,RMTS 项目继续为学术天才学生提供评估、表彰和暑期强化课程。如今,RMTS 已进入第 23 个年头,正蓬勃发展,并每年扩展其提供的服务。
Wallace 2005
「为资优学生提供的远程教育:利用技术扩展学术选择」,Wallace 2005:
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接入正在促进超越传统面对面课堂环境的新型教育方法。对于那些需求在课堂上更难满足的一些特殊学习者群体而言,远程教育已成为一个宝贵的选项,而资优学生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了远程教育的多种形式及其支持技术,并审视了关于这些方法在不同情境下有效性的研究。文章总结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青少年中心提供的远程教育项目的研究成果,并基于这些发现,提出了最佳实践。
Brody 2005
「卓越才能研究」,Brody 2005:
卓越才能研究项目(SET)识别出展现出极高数学和/或言语推理能力的学生,并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需要的、富有挑战性的教育项目,以实现其全部潜力。具体而言,那些在 13 岁之前在 SAT I 的数学或言语部分得分在 700–800 分的学生被邀请利用 SET 的咨询和辅导机会。一项持续的纵向研究追踪着这些学生的进展,他们迄今为止的成就非同寻常。作为一个群体,SET 的学生参加各种加速项目,就读于高度选择性的学院和大学,并大量获得高等学位。那些已经步入职业生涯的人似乎也在他们选择的领域中表现卓越。
Brody & Mills 2005
「天才搜寻研究:我们学到了什么?」,Brody & Mills 2005
本章总结了从天才青少年中心超过 25 年的研究,以及此前由 Julian Stanley 博士及其研究生们进行的10年研究所学到的经验教训。本总结亦涵盖了其他几大天才搜寻项目(杜克大学、西北大学和落基山项目)所做的工作,尽管对他们工作的完整描述可以在他们各自撰写的单篇文章中找到。来自数百项研究的发现验证了天才搜寻的识别模型和过程,以及为满足被识别学生的需求而开发的项目。此外,作者们浓缩了来自众多研究项目的发现,这些项目审查了 CTY 所服务的学生的认知、社会、个性和学业发展。
Gilheany 2005
「爱尔兰天才青少年中心」,Gilheany 2005:
对青霉素进行效力测试,与 NASA 宇航员讨论火箭技术,分析中世纪时期的动物骨骼碎片——这些只是爱尔兰天才青少年中心学生们日常活动的一部分。该中心识别具有卓越学术能力的年轻学生,然后为他们、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提供服务。本文重点介绍了该中心的工作,特别是在早期培养和发展对科学的兴趣方面。
Touron 等人 2005
「西班牙天才青少年中心:一项服务高能力学生的主动计划」,Tourón 等人 2005:
本文论述了西班牙天才青少年中心自成立以来所开展工作的主要方面。此处应用的教育模式,基于由 Julian Stanley 在七十年代初开发的「数学超常青年研究」项目,该模式目前是所有属于国际天才青少年中心的中心的灵感来源。我们提供了来自 SCAT(「学校和大学能力测试」)测试的数据,该测试由第一作者在西班牙完成验证,用于识别具有卓越言语或数学能力的学生。获得的结果在理论模型的背景下进行了分析,强调了获得的结果与在美国的结果之间的相似性。此外,我们探讨了关于课程开发和学生对课程评估的数据。最后,我们探讨了该中心和西班牙高能力学生的未来前景。
Frost 2005
「CTY 暑期学校模式:在英格兰国家天才青年学院的演进、适应与外推」,Frost 2005:
本文比较了由英格兰国家天才青年学院(NAGTY)举办的暑期学校与由美国天才青少年中心(CTY)举办的暑期学校。当 NAGTY 暑期学校开始时,它们基于 CTY 模式,但该项目在过去三年的运营中已经演变。本文着眼于基本设计、课程、学生、暑期学校地点和教学法问题。还有一个广泛的部分分享了关于 2004 年 NAGTY 项目的评估数据。文章中表达的压倒性观点是,这是两个非常成功的项目,深受学生和评估者的高度赞誉。正如参加过两者的学生所评论的,暑期学校有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但质量都很高。他们在暑期学校的经历对学生来说是改变人生的。他们从经历中走出来,变得更加自我导向,并有更高的抱负和期望。NAGTY 和 CTY 有一些有趣的计划来进一步发展暑期学校模型。随着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开发类似的项目,未来是令人兴奋的。通过持续合作,各方都能相互借鉴,并在现有的高质量经验基础上再接再厉。
Touron 2005b
「已竟之业,未竟之功」,Tourón 2005b [结束语]
Wai 等人 2005
「智力超常青少年的创造力与职业成就:一项从 13 岁到 33 岁的纵向追踪研究」, Wai 等人 2005:
本研究对智力超常的青少年(能力排名前 1%)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第一阶段(n = 1243 名男孩,732 名女孩)旨在考察,在该顶尖群体中,13 岁时的能力差异对于预测其未来获得博士学位、收入水平、专利数量以及在美国排名前 50 的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重要性。研究第二阶段(n = 323 名男性,188 名女性)则评估了早前一项研究建立的判别函数的稳健性。该判别函数基于 13 岁时的能力与偏好评估,并以 23 岁时的教育成就作为校准标准,而本研究将其应用范围拓展至预测研究对象在 33 岁时的职业归属。通过《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进行的超纲测试以及传统的个人偏好量表在教育情境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同样适用于职业情境。天赋的早期展露预示着个人未来在职场上将取得卓越的成就和非凡的创造力;而当天赋与个人偏好相结合时,还能预测这些成就的具体性质。
Benbow & Lubinski 2006
「讣告:朱利安·C·斯坦利(1918–2005)」, Benbow & Lubinski 2006
《观察家》2005
「缅怀:朱利安·斯坦利」,《观察家》:由David Lubinski(「一位仁爱且富有同情心的学术巨匠」)、Nicholas Colangelo(「致敬朱利安」)、Nancy M. Robinson(「追求卓越,永无止境」)、Arthur R. Jensen(「斯坦利与特尔曼:天才研究领域的双子星」)以及Camilla Persson Benbow(「一位卓越的美国智者」)为朱利安·C·斯坦利撰写的悼文。
Lubinski & Benbow 2006
「数学超常青年研究 35 年回溯:揭示数学与科学专长形成的前因」, Lubinski & Benbow 2006:
这篇综述报告了「数学超常青年研究」(SMPY)在历经 35 年纵向研究后取得的成果。报告呈现了来自三个队列近期的 20 年追踪数据,以及 SMPY 所有五个队列(总参与人数逾 5000 人)的 5 年或 10 年研究发现。
SMPY 项目尤其致力于揭示在数学和科学领域取得卓越职业成就所需的个人先决条件,并开发相应的教育干预措施以促进智力超常青少年的学习进程。研究发现,除了数学天赋外,高水平的空间能力、探索型兴趣和理论型价值观共同构成了一套极具潜力的资质组合,这预示着个人发展科学专长的巨大潜力以及对科学事业的持久热忱。当然,特殊的教育机会能显著地促进才能的绽放。此外,非凡的科学成就离不开在校内外付出的超常努力。
「工作适应理论」(TWA)为我们构想人才的识别与发展,以及衔接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框架。借助TWA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某些性别差异在教育和职业领域是如何显现的。例如,在 SMPY 的队列中,尽管投身于数学和科学事业的男性天才多于女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因为这些女性在更契合其多维度能力与偏好模式的领域(如行政管理、法律、医学和社会科学)同样取得了相当比例的高级学位和高阶职位。步入三十五岁左右时,无论男女,他们似乎都对各自的人生抉择感到满意,并认为自己同样成功(客观的衡量指标也印证了这些主观感受)。在现代文化中,定量和科学推理能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当数学天才选择在工程和物理科学以外的领域发展事业时,我们应将其视为对社会的贡献,而非人才的流失。
Lubinski 等人 2006
「追踪卓越人力资本二十载」, Lubinski 等人 2006:
本研究对一批在 13 岁前经认知能力测试鉴定为顶尖 0.01% 的「英才探寻计划」参与者(286 名男性,94 名女性)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追踪。我们将他们的创造力、职业成就和人生发展,与1992年进入美国顶尖大学数学、工程和物理科学专业就读的研究生(299 名男性,287 名女性,已追踪 10 年)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到三十五岁左右时,这两个群体都取得了同等水平的卓越成就(例如,获得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终身教职),并且对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有着同样高的满意度。这项研究表明,对智力超常的青少年进行大学入学水平的测试,能够发掘出他们在信息时代从事需要创造力和科技创新的职业时所具备的非凡潜力。
[另请参阅 「看不见的天才:知识前沿能否加速拓展?」,Agarwal & Gaule 2018,该研究在极具数学天赋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竞赛选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能力梯度:金牌得主荣获菲尔兹奖的概率,是美国排名前十的数学项目毕业生的 50 倍。Gasser 2019 则以一支匈牙利 IMO 代表队为个案进行了深入研究。]
Muratori 等人 2006
「来自 SMPY 昔日顶尖神童的启示:Terence (‘Terry’) Tao 博士与 Lenhard (‘Lenny’) Ng 博士反思其才能发展之路」, Muratori 等人 2006: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现有的教育实践满足天赋异禀的学生的学术需求,那么天才教育专家便可推断,对于那些能力稍逊但同样才华横溢的学生,我们也可以通过组合运用这些策略来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本文通过重点介绍两位顶尖数学神童的独特教育历程,阐明了为天才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教育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这两位神童是 Julian Stanley 博士自 1971 年创立「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以来所发掘的最杰出的人才。我们完整呈现了对 Terence (“Terry”) Tao 博士和 Lenhard (“Lenny”) Ng 博士的访谈内容,他们如今都已是成就斐然的数学家。访谈表明,即使是面对最顶尖的天才,只要有富于创造力的规划,并得到家长、教育者和导师的通力合作,我们依然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打造有效的培养策略。
Brody 2007
「引导高天赋学生善用补充性教育机会:以SET项目为范例」, Brody 2007, 载于 VanTassel-Baska 2007 年主编的《超越传统课堂:服务天才学习者》。
Halpern 等人 2007
「科学与数学领域性别差异的科学探究」, Halpern 等人 2007:
在公众对科学与数学领域职业性别差异的原因众说纷纭之际,我们基于现有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发布一份共识声明。在能力分布的中等区间,科学与数学成就和能力的性别差异,要小于高成就和高能力群体的性别差异。在大多数定量和视觉空间能力的测量中,男性的变异性更大,这必然导致在高能力和低能力两端都存在更多的男性;而男性为何通常更具变异性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在数学和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职业生涯需要多种认知能力。女性倾向于在语言能力方面表现更优,当评估包含写作样本时,两性间的差异尤为显著。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取得高水平成就需要有效的沟通能力和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力,因此女性在写作方面的优势应在所有学术领域中都有所助益。在大多数视觉空间能力的测量中,男性表现优于女性,这被认为是造成男女在数学和科学标准化考试中分数差异的原因之一。关于数学和科学领域性别差异的进化论解释支持以下结论:尽管数学和科学表现上的性别差异并非直接演化的结果,但它们可能与兴趣以及特定的大脑与认知系统差异间接相关。我们回顾了科学和数学领域性别差异的神经基础,描述了一系列一致的效应,并指出了众多可能的关联因素。经验能够改变大脑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将大脑差异归因于数学和科学成就的因果论断本身是循环论证。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促成了数学和科学成就与能力的性别差异,这包括家庭、社区、同伴和学校的影响,以及培训、个人经历和文化习俗。我们的结论是,早期经历、生物因素、教育政策和文化背景共同影响着投身科学和数学高等研究的男女性数量,且这些因素以复杂的方式叠加并相互作用。关于科学与数学领域性别差异的复杂问题,不存在任何单一或简单的答案。
Lubinski & Benbow 2007
「发展科学专长所需个人特质的性别差异」, Lubinski & Benbow 2007, 载于 Ceci & Williams 2007年主编的《为何科学界女性寥寥?顶尖研究者激辩证据》:
我们的社会日益趋向科学化、技术化和知识化,其发展依赖于对人类才华与潜能的充分利用和最大化(Friedman, 2005)。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公民实力,现已与其能从民众智慧中激发何种创造力紧密相连。因此,如何增加美国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专业人才的数量,以及如何发掘潜在的人才储备库,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政策若要行之有效,必须建立在对如何在STEM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深刻理解之上。在此,我们回顾一系列已知的影响个人在数学与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和保持热情的先决条件。我们尤其关注在这些特质上已有充分文献记载的性别差异,及其对STEM学科中男女比例的影响。我们并不侧重于讨论教育经历和机会,例如合适的进阶安排(Benbow & Stanley, 1996; Bleske-Rechek, Lubinski, & Benbow, 2004; Colangelo, Assouline, & Gross, 2004; Cronbach, 1996; Lubinski & Benbow, 2000; Stanley, 2000)或参与科研(Lubinski, Benbow, Shea, Eftekhari-Sanjani, & Halvorson, 2001),尽管这些对于在STEM领域培养人才至关重要;相反,我们聚焦于那些促使个体追求并在STEM职业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个人特质(Lubinski & Benbow, 1992; Lubinski, Benbow, Webb, & Bleske-Rechek, 2006; Wai, Lubinski, & Benbow, 2005)。本文也并非旨在探讨如何提升美国普通大众的科学素养。该议题虽至关重要,但与本文主旨——培养顶尖的STEM专业人才——有所不同。通过我们的「数学超常青年研究」(SMPY),我们专注于后者(Benbow, Lubinski, Shea, & Eftekhari-Sanjani, 2000; Lubinski & Benbow, 2000, 2001; Lubinski, Benbow, et al 2001; Lubinski et al 2006; Wai et al 2005; Webb, Lubinski, & Benbow, 2002),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本次综述。正如SMPY项目所实践的,聚焦于才华出众的群体是恰当的,因为大多数STEM专业人才都来自能力排名前10%的人群(Hedges & Nowell, 1995)。
Park 2007
「迥异的智力模式可预测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创造力:一项对智力超常青年长达25年的追踪研究」, Park 2007:
……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便是在能力排名前1%的顶尖群体内部,个体差异也能预测其在职业表现和创造力上的不同:能力更强者,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取得终身教职、赚取高薪以及获得专利等成就的可能性也更高(Lubinski, Benbow, Webb, & Bleske-Rechek, 2006; Wai, Lubinski, & Benbow, 2005)。然而,大多数标准化评估都难以区分「有能力」和「极具能力」的人,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大学入学考试等传统指标上往往都会触及分数「天花板」。高端分数的区分度不足,限制了这些评估指标与未来成就之间的关联性。然而,若在这些智力超常的青少年13岁前对他们进行大学入学水平的测试,其分数分布便会与典型的即将升入大学的12年级学生相似,从而能轻易地区分出「有能力」和「极具能力」者(Lubinski & Benbow, 2006)。当对这些青少年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后,我们便能评估能力排名前1%(该范围覆盖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能力区间)的个体差异所具有的心理学意义。例如,排名前1%人群的智商约从137起步,最高可超过200。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样需要有高「天花板」的成就标准,才能对这些早期评估的有效性进行纵向评价(同时,追踪的间隔时间也必须足够长,以确保个体有时间发展出取得创造性成就所需的专业知识)。
在本研究中,我们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说:在能力排名前1%的智力超常青少年中,他们于12岁时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数学和言语推理能力模式,可以差异化地预测其25年后在人文学科与STEM领域的创造性成就。
Park 等人 2007
「迥异的智力模式可预测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创造力:一项对智力超常青年长达25年的追踪研究」, Park 等人 2007 (预印本):
本研究对2409名在13岁前参加SAT评估的智力超常青少年(能力排名前1%)进行了超过25年的纵向追踪。我们以他们的创造性成就(尤其侧重于文学成就和科技创新)为因变量,考察了其能力水平(SAT数学与言语分数之和)和能力倾向(SAT数学分数减去言语分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13岁前就已显现的独特能力模式,预示了他们在中年时期截然不同的创造性表达形式。能力水平固然对创造性成就有重要贡献,但能力倾向对于预测成就发生的具体领域(例如,是在人文学科还是在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领域获得终身教职;是出版一部小说还是获得一项专利)则更为关键。
Park 等人 2008
「学历相当,能力差异对科学创造力依然重要」, Park 等人 2008:
本研究对1586名在13岁前参加SAT数学部分评估的智力超常青少年(能力排名前1%)进行了超过25年的追踪。我们以其获得的专利和发表的科学论文作为衡量其科技成就的标准。参与者根据其最终学位(学士、硕士或博士)进行分组。在各个学位组内部,成年后至少拥有一项专利或一篇科学论文的参与者比例,会随着其早期SAT成绩的提高而增加。这表明,有关认知能力的个体差异信息(即便是在青少年早期测得),能够预测在拥有同等高等教育学位的人群中,其在科技领域创造潜力的差异。
Swiatek 2007
「英才探寻模式:过去、现在与未来」, Swiatek 2007:
常规的标准化成就测试无法准确评估天才学生的能力,因为这些测试对他们而言缺乏足够的挑战性。「英才探寻计划」通过「超纲测试」——即使用为高年级学生设计的试题来为低年级天才学生提高测试难度上限——解决了这一问题。目前,「英才探寻计划」为美国本土及数个海外国家的2至8年级天才学生提供服务。大量研究表明,「超纲测试」的成绩能够有效区分不同层次的天赋水平,并对教育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得分高的学生能迅速且出色地掌握高阶知识,并在加速学习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因此,「英才探寻计划」在测试之后,还提供了一系列教育项目,其中许多侧重于加速学习。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项目为参与者带来了学术和心理社会双方面的益处。或许,「英才探寻计划」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在学校环境中促进对天才学生的因材施教。
Webb 等人 2007
「空间能力:智力超常青年英才探寻计划中被忽视的维度」, Webb 等人 2007:
本研究旨在探究空间能力是否能揭示个体在数学与科学领域的潜力,研究对象为通过「英才探寻计划」筛选出的学生。在第一阶段,我们比较了智力超常的青少年(617名男孩,443名女孩)与顶尖的数理科学研究生(368名男性,346名女性)在兴趣和价值观上的异同,并结合他们的空间想象能力,以评估他们与数理科学职业的潜在契合度。在第二阶段,一项为期五年的纵向分析显示,空间能力与一系列预示着适合从事科学事业的个人偏好特质相辅相成,并且在预测数理科学领域的成就时,其预测效力超出了个人偏好的范畴。在第三阶段,我们对拥有《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成绩的参与者数据进行了纵向分析,再次发现了一个显著的「数理科学特质组合」(其中,空间能力和SAT数学成绩与之持续正相关,而SAT言语成绩则与之负相关)。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表明将空间能力纳入当前的「英才探寻计划」识别程序(目前仅限于数学和言语能力),不仅能发掘出一个被忽视的数理科学人才库,还有望加深我们对智力超常青少年的理解。
Leder 2008
「数学优等生:我们能从他们身上以及关于他们学到什么?」, Leder 2008:
数学上的成功被广泛视为通往许多专业课程和职业道路的重要门槛。但是,在校期间的数学优异表现真的会影响个体的教育和职业轨迹吗?天赋出众的数学学生是否有着独特的工作习惯?他们是被数学密集型领域所吸引,还是更倾向于转向其他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学时期即被公认为数学优等生的群体进行调研,探讨了这些及相关问题。[澳大利亚数学竞赛(AMC)]
以往研究回顾:对包括数学优等生在内的杰出人才的发展历程,学界已进行了持续而多样的研究。「数学超常青年研究」[SMPY]由Julian Stanley于1971年创立,催生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这些文献涵盖了从阐述该项目理论基础及早期参与者研究发现的出版物(例如,Stanley, Keating, & Fox, 1974),到近期记录参与者长期个人成长、教育背景及成年后职业成就的文献。正如Lubinski, Benbow, Webb, 和 Bleske-Rechek(2006)所指出的,许多后期文献关注的是那些「在13岁之前……其SAT数学推理能力(SAT-M ≥ 700)或SAT言语推理能力(SAT-V ≥ 630)得分位列同龄人前0.01%」的学生(第194页)。其他研究者也探讨了高能力数学学生的发展路径和工作偏好。
Benbow & Lubinski 2009
「将Sandra Scarr的发展理论应用于智力超常青年的纵向研究」, Camilla P. Benbow & David Lubinski 2009:
Sandra Scarr将其整个职业生涯奉献给了将人类个体性科学应用于全生命周期的发展议题(Scarr, 1992, 1996; Scarr & McCartney, 1983)。揭示人类个体性的科学,以及通过研究人类心理多样性所展现出的差异化发展结果,这条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Scarr, 1992, 1998),但它对于应用心理学和基础心理学(Lubinski, 1996, 2000; Underwood, 1975),以及对于制定旨在改变人类行为的有意义的公共政策,几乎总是有益的(Scarr, 1996)。尽管如此,对人类个体性的有效测量及其评估所获得的科学知识所具有的心理学重要性,却常常遭到否认或忽视。
在本章中,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我们将阐述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人类个体性的研究发现被频繁否定或忽视的现象有多普遍,以及这种现象如何阻碍了对真正卓越的人力资本的识别与培养,并妨碍了对非凡人类成就的建模。其次,我们将概述Scarr关于「生态位建构与选择」的理论(Scarr, 1996; Scarr & McCartney, 1983)的价值,并说明从心理学视角研究环境如何能启发我们为天赋异禀的学生创造更优化的学习机会(Benbow & Lubinski, 1996; Benbow & Stanley, 1983; Benbow & Stanley, 1996; Stanley, 2000)。这样做,同时也为我们洞察他们的终身学习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Brody 2009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才探寻模式:识别与发展杰出数学及言语才能」, Brody 2009:
由Julian Stanle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创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才探寻模式,现已推广至世界多国。该模式亦被称为人才发展的「MVT:D4模型」,其在识别和服务于具有超常数学和/或言语推理能力的学生方面的强大能力与功效已得到充分验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其他采用此模型的高校的研究人员,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天才学生需求的知识与理解。他们还开发并评估了众多策略,以满足这些高能力学生的教育需求。本章将对英才探寻模式的历史、原则、实践及其相关的学生研究进行总结。
Ferriman 等人 2009
「顶尖数理研究生与极具天赋者的工作偏好、人生观与价值观:成年早期与为人父母后的发展变化及性别差异」, Ferriman 等人 2009:
本研究评估了顶尖数理科学领域的研究生(275名男性,255名女性)在25岁和35岁时的工作偏好、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研究一中,对工作偏好的分析揭示了其优先级随年龄发展的变化及性别差异:某些性别差异随时间推移而扩大,且在已为人父母的参与者中比无子女者更为显著,这似乎是由于成为母亲后其优先级发生了改变。在研究二中,我们将35岁时研究生的性别差异与另一组极具天赋的参与者(能力排名前万分之一,自13岁起追踪20年:265名男性,84名女性)进行了比较。结果再次显示,已为人父母者中的性别差异更大。在两个队列中,男性似乎都比女性更倾向于一种主动进取、以事业为中心的视角,他们更看重创造高影响力的成果、获得丰厚报酬、勇于承担风险以及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而女性则似乎更青睐一种更具社群性、着眼全局的视角,她们更强调社群、家庭、友谊,并希望投入较少的时间在事业上。人生优先级的性别差异在为人父母后会加剧,这预示了即使在能力、职业兴趣和教育背景相似的才俊男女中,他们未来在高阶和高强度职业中的性别比例也会有所不同。
Lubinski 2009a
「认知流行病学:重点厘清认知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纠葛」, Lubinski 2009a:
本评论探讨了认知流行病学在实践、公共政策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启示,并整合了这期重要特刊中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正如本特刊及其他研究(Deary, Whalley, & Starr, 2009; Gottfredson, 2004; Lubinski & Humphreys, 1992, 1997)所明确指出的,社会科学家和实践者在构建流行病学和医疗健康现象的模型时,绝不能忽视认知能力的作用。然而,鉴于学界普遍担忧一般认知能力(GCA)与社会经济地位(SES)之间存在混淆效应,且常将SES视为导致健康差异的主因(而GCA在流行病学和健康心理学中作为潜在影响因素却被忽视),本文回顾了一些旨在厘清GCA和SES相对影响的方法论应用。此外,本文将认知流行病学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正如认知流行病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病理状态(识别「高风险」人群,并寻求方法减弱不良的个人及社会状况),它同样能丰富我们对最佳功能(识别「高潜力」人群,并寻求方法识别和培育所需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以创造革新,拯救生命、经济,乃至我们的星球)的理解。最后,尽管GCA可能是研究个体差异以构建健康行为和结果模型时最重要的维度,但其他相对独立的心理多样性维度确实也能提供额外的价值(Krueger, Caspi, & Moffitt, 2000)。例如,依从性至少包含两个心理要素:一个「能做到」的能力要素(能力)和一个「会去做」的动机要素(尽责性)。归根结底,要开发和模拟健康行为、人际环境及医疗问题,最好是整合人类个体性的多个维度来进行。
Lubinski 2009b
「超常认知能力:其表型特征」, Lubinski 2009b:
近年来,由于现代「英才探寻计划」识别出大量智力超常的青少年,并对他们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纵向追踪,使得系统描绘超常认知能力这一表型所对应的发展结果成为可能。认知能力的水平与模式,即便是在普通智力水平位列前1%的群体内部,也与个体差异化的发展轨迹和重要的人生就有关:获得博士学位、赚取丰厚报酬、出版小说、取得专利、在顶尖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以及最可能获得教职的学科领域),这些成就的概率都与数十年前所评估的个体认知能力差异相关。青少年早期区分「有能力者」(百里挑一)与「极具能力者」(万里挑一)的个体差异对人生产生深远影响。鉴于一般智力的遗传性,这表明理解超常能力的遗传与环境起源,应成为行为遗传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因为极端群体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普通人群有所不同。此类研究除了能增进我们对极端智力水平成因的理解外,还可能揭示特定能力(如数学与言语推理能力)的根本决定因素,以及不同能力模式在超常水平上最可能最终形成的独特表型特征。
Wai 等人 2009
「STEM领域的空间能力:整合逾50年心理学知识,彰显其重要性」, Wai 等人 2009:
本文探讨了空间能力在教育追求和职业领域中的重要性,尤其关注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研究参与者选自一项对美国高中(9-12年级,n = 400,000)进行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对他们进行了长达11年以上的追踪;其纵向研究结果与1957年之前的研究发现以及来自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和「数学超常青年研究」[SMPY]的当代数据进行了比对。数十年的研究一致表明,青少年时期测得的空间能力,是那些日后在STEM领域取得高等教育文凭和职业成就的个体所共有的一个显著心理特质。研究结果巩固了以下结论:空间能力在培养STEM专业知识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启示我们,将空间能力纳入现代的英才探寻计划,将能识别出大量目前被遗漏的具有STEM潜力的青少年。
Park 等人 2009
「认识空间智能: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必须更重视空间推理这一关键智能」,Park 等人 2009(《科学美国人》):
……近期关于认知能力的研究正在印证一些心理学家数十年前的观点:空间能力,又称空间想象能力,在工程学和科学学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更侧重于言语能力的智商测试,以及当今许多流行的标准化考试,都未能充分评估这一特质,尤其是在那些最具此项天赋的人群中。
……最近一篇发表于《教育心理学杂志》的综述,分析了两项大型纵向研究的数据。杜克大学的Jonathan Wai与我们中的两位(Lubinski和Benbow)合作,揭示了忽视空间能力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在这两项研究中,参与者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包括空间能力在内的多项能力评估。那些空间能力相对较强的参与者,往往倾向于投身并擅长于物理、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科技领域。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排除了长期以来被认为能预测教育和职业成就的定量与言语能力之后,这一趋势依然存在。在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增加STEM领域学生数量的巨大压力之际,将空间能力的知识融入当前的教育实践和英才探寻计划,或许是提升这些努力成效的关键所在。
……由于学校课程、传统标准化评估以及国家英才探寻计划对空间能力的忽视,在整个能力谱系中拥有相对空间优势的群体,构成了一个服务不足的潜在人才库,他们本可为当前的科技劳动力注入强大动力。Alvarez和Shockley尽管未被特尔曼的英才搜寻计划发现,但他们最终还是凭借自身努力取得了成功,并对上个世纪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我们究竟错过了多少个像Alvarez和Shockley这样的天才呢?鉴于科技创新能够改善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只错过一个,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Wai 等人 2009b
「融合潜力与热情,共创美好未来:一项智力超常青年的教育模型」, Wai 等人 2009b (载于 Renzulli 等人 2009 主编, 《天才与优才项目开发系统与模型(第二版)》):
要想为智力超常的学生最优地开发和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项目,教育者首先需要认识到一个对所有学生都至关重要的概念,即他们心理多样性的本质与范畴——也就是他们的个体性。这一术语源自E. L. Thorndike于1911年发表的里程碑式文章的标题,正是这篇文章将对个体差异的重视引入了美国心理学(Dawis, 1992)。本质上,项目设计应将学习机会与每位学生的个体特征相结合(Lubinski & Benbow, 2000, 2006)。换言之,教育应当将个体的潜能(能力)与热情(偏好)相融合,为每位学生独特的潜力(即学习准备度)量身定制教育体验。这种由不同的能力/偏好组合模式所产生的差异化发展潜力,在「特质簇」(Ackerman, 1996)、「资质组合」(Corno, et al 2002; Snow, 1991)和「分类单元」(Dawis & Lofquist, 1984)等综合概念中得以体现。其核心思想是,了解一个人能做什么(能力或才能)只是等式的一半;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他/她会做什么或想做什么(即兴趣、需求和价值观)……我们用以支持我们模型的主要纵向数据,来源于「数学超常青年研究」(SMPY)。
Steenbergen-Hu 2009
「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的影响:一项元分析」, Steenbergen-Hu 2009 (学位论文):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综合了当前关于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学业成就及社会情感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共纳入1984年至2008年间进行的38项原始研究。所有纳入的研究均经过仔细审查,以确保接受加速学习的高能力学习者与恰当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研究采用Hedges’s g作为主要的效应量指标。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假定效应会因情境、干预条件和/或受试者的不同而变化。首先,我们分析了加速学习的总体效应。随后,根据发展阶段(学前至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和对照组类型(加速学习者是与同龄、年长还是混合年龄的同伴进行比较)对结果进行分类讨论。此外,研究还进行了旨在识别潜在调节变量的分析。最后,我们从实践意义的角度对结果进行了解读,并与以往相关的元分析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
在学业成就方面,本次元分析的发现与以往元分析的结论一致,即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有积极影响。按发展阶段对学业成就效应进行分类后,发现在两个阶段均存在积极效应。在与未接受加速学习的同龄同伴进行比较时,加速学习对学业成就的积极效应始终高于其他对照组,这表明与同龄人相比,加速学习的优势可能更为明显。此外,研究发现加速学习的持续时间和所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学业成就效应的调节变量。
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社会情感发展的影响似乎也略呈积极,尽管其积极效应的强度不及学业成就。然而,与以往的元分析研究相比,本研究对加速学习在社会情感发展方面的影响得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印象。
Steenbergen-Hu & Moon 2010
「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的影响:一项元分析」, Steenbergen-Hu & Moon 2010 (Steenbergen-Hu 2009 学位论文的期刊文章版本):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综合了当前关于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学业成就及社会情感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研究共纳入1984年至2008年间进行的38项原始研究。我们根据发展阶段(学前至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和对照组类型(加速学习者是与同龄、年长还是混合年龄的同伴进行比较)对结果进行了分类讨论。研究结果与以往元分析的结论一致,表明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的学业成就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随机效应模型下,g = 0.180, 95% CI = -0.072, 0.431)。此外,其对社会情感发展的影响也似乎略呈积极(在随机效应模型下,g = 0.076, 95% CI = -0.025, 0.176),尽管其强度不及学业成就。研究并未发现有关效应调节变量的强有力证据。
研究成果的应用:本次元分析的结果表明,加速学习对高能力学习者有着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学业成就方面。这对教育者、家长和学生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高能力学习者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能从加速学习中获益。具体而言,在标准化成就测试、大学成绩、所获学位、就读院校的声望以及职业地位等方面,接受加速学习的学生往往优于未接受者。在自我概念、自尊心、自信心、社会关系、课外活动参与度以及生活满意度方面,加速学习者与非加速学习者表现相当或更优。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本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加速学习项目,特别是大学主办的少年班等提前入学项目,经过了频繁的评估,并似乎是最有效的形式。总而言之,无论是在K-12基础教育还是在大学阶段,加速学习都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我们鼓励家长为有学术天赋的子女考虑加速学习,也鼓励教育者提供加速学习的选择。
2010
Henshon 2010
「非凡的天才发掘者:Camilla P. Benbow 访谈录」, Henshon 2010
Lubinski 2010
「空间能力与 STEM:人才识别与发展中沉睡的巨人」, Lubinski 2010:
空间能力是个体差异的一个强大且系统性的来源,但在复杂的学习和工作情境中,它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构建专业知识发展与创造性成就的模型时,它也同样被忽略。然而,长达五十余年的纵向研究记录表明,空间能力在教育和职业领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些领域,运用图形、模式和形状进行复杂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在信息时代大力推动培养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的背景下,我们正迎来一个凸显空间能力心理学意义的良机。这样做不仅有望为「因材施教」(aptitude-by-treatment interactions)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也为实践 Underwood (1975) 将个体差异作为理论构建熔炉的理念提供了参考。在为进阶学习机会选拔人才时纳入空间能力的考量,能够发掘出一个尚未被充分利用的人才库,以满足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复杂需求;反之,在为 STEM 领域的进阶学习机会选拔学生时若不考虑空间能力,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对学生造成伤害。
Robertson 等人 2010
「打破『能力门槛』假说:即使在天才和顶尖数理研究生中,认知能力、职业兴趣及生活方式偏好依然对职业选择、表现和毅力有重要影响」, Robertson 等人 2010:
那种认为能力差异在超过某一阈值后便不再重要的论断是不准确的。在定量推理能力位居前 1% 的青少年中,他们的一般认知能力水平以及特定认知能力模式(即个人在数学、言语和空间能力上的相对强弱)的差异,会对其数十年后的教育、职业和创造性产出造成影响。其中,能力水平预示着成就的高度,而能力模式则预示着成就的领域。若再结合职业兴趣方面的信息,便可以更精确地预测其教育和职业选择。最后,与职业选择、表现和毅力相关的生活方式偏好通常在 25 至 35 岁之间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偏好上的性别差异,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那些要求超负荷工作(每周超过 40 小时)的职业中,女性的代表性不足。
图 1:在 13 岁时被识别,超过 25 年后,数学推理能力顶尖 1% 人群内部不同个体成就的差异。来自「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第 1、2、3 批(N = 2,385)的参与者,根据其 13 岁时的 SAT-M(数学)分数被分为四分位数。这四个分位数沿 x 轴按其平均 SAT-M 分数标示。认知能力排名前 1% 的分数线为 390 分,满分为 800 分。图中每条标准线的末尾都标示了比值比(OR),用于比较最高分位(Q4)与最低分位(Q1)在各项成就上的几率。星号(*)表示 Q4 组在该项成就上的几率在统计上显著高于 Q1 组。STEM 指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STEM 教职(前 50)指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7 年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中位列前 50 的美国高校的 STEM 领域终身教职。部分改编自 Park、Lubinski 和 Benbow (2007, 2008) 的研究。
Wai 等人 2010
「STEM 领域的成就及其与所受 STEM 教育剂量的关系:一项长达 25 年的纵向研究」, Wai 等人 2010:
两项研究探讨了大学前的强化/拓展教育经历与成年后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取得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一中,1,467 名 13 岁学生因其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数学部分得分不低于 500 分(排名前 0.5%)而被认定为数学天才;此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发展轨迹进行了长达 25 年的追踪。研究特别关注了在普通人群中出现率极低的 STEM 高水平成就(如 STEM 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发表、终身教职、专利和从业情况)。研究二则回顾性地分析了 714 名顶尖 STEM 研究生(平均年龄 25 岁)在青少年时期的强化/拓展教育经历,并将其与他们到 35 岁时在 STEM 领域的成就进行关联分析。在这两项纵向研究中,取得卓越 STEM 成就的个体,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大学前 STEM 强化教育机会的密度(即更高的「STEM 剂量」)都显著高于同批次中成就相对较低的成员。尽管这两项研究均为准实验性研究,但其结果表明,对于数学天赋出众且学习动机强的青少年而言,丰富多样的、旨在提供智力挑战(即使对这些早慧学生而言也是如此)的大学前 STEM 教育机会,能够促进他们未来的成就。这些机会对男女两性似乎同等重要。
Hunt 2011
《人类智能》,Hunt 2011 (ISBN 978-0-521-88162-3)。教科书:第 10 章,「智力有何用处?」(该章节回顾了 SMPY 项目,以及其他证明智商预测有效性的相关研究,如 Terman 的研究、“十万新兵计划”和“兵役职业能力倾向成套测验” (ASVAB) 的计分失误事件)
Touron & Touron 2011
「天才儿童中心的人才识别模型:文献综述」, Tourón & Tourón 2011:
本文回顾了关于「天才搜寻计划」人才识别模型的文献。该模型由 Julian Stanley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学早慧青年研究」项目中首创,并自 80 年代初至今由天才儿童中心(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付诸实施。美国其他大学也采纳了此模型进行人才识别与培养,它还被调整后应用于其他国家。迄今,已有超过 350 万名学生参与了「天才搜寻计划」的评估,数十万名学生入读了为优等生设计的专门学术课程。本文分析了该模型的创始原则、普适性特征及其在西班牙的应用与运作情况。最后,我们就此模式带来的启示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前景提出了一些思考。
Touron & Touron 2016
「言语与数学才能的识别:『超纲』测评的重要性」,Tourón & Tourón 2016:
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目标。其一,对国际文献中所谓的「天才搜寻计划」模型或概念进行概念性梳理,并结合本研究作者在西班牙的相关工作进行回顾。该模型由 J. C. Stanley 在 70 年代初创立,极大地推动了青少年言语和数学才能的识别工作,以便为他们提供其能力发展所需的恰当教育支持。本文旨在证明,这远非一个仅适用于美国的模型——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通过展示该模型在西班牙多年实施的数据,我们认为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普适模型。其核心原则之一便是采用超前或「超纲」的测评方式。通过这种超纲测评,我们能有效地区分出受试学生之间不同的能力水平;若仅使用同年级水平的测试,由于试卷缺乏足够的难度和区分度,这些能力差异往往会被掩盖。文中还为在学校大规模推广这些测评程序提供了一些建议。
Benbow 2012
「识别并培养 STEM 领域的未来创新者:来自『数学早慧青年研究』的发现回顾」, Benbow 2012:
就业趋势以及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创新对经济的重要性,共同凸显了加强 STEM 教育的迫切性。「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对超过 5000 名天才个体进行了长达 40 年的纵向追踪,为解答 STEM 领域人才识别与培养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深刻见解。SMPY 的研究对象包括在七、八年级时被识别出数学或言语能力排名前 1% 或更高的个体,以及一组由顶尖 STEM 研究生构成的对照组。SMPY 的研究发现涵盖了参与者的教育与职业成就,其中有很高比例的人获得了学位或在 STEM 领域从事着极具影响力的职业;研究还揭示了性别差异、高中时期的经历、能力和兴趣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程度,以及他们后来的创造性产出。通过标准化考试测得的数学推理能力,是预测成年后在数理科学领域参与度和成就的可靠指标,而空间能力则能提供额外的预测价值。获得恰当的教育机会确实与职业成就及创造性产出呈正相关。SMPY 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未来的 STEM 潜在创新者可以被早期识别,而教育干预能够增加他们成功的几率。
Kell & Lubinski 2013
「空间能力:教育与职业领域中被忽视的天赋」, Kell & Lubinski 2013 (综述):
过去 60 余年间,针对数万名高能力和智力早慧青年的纵向研究一致表明,空间能力对于需要动手实践的创造性成就,以及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中培养专业知识至关重要。然而,空间能力的个体差异在教育咨询和选拔中却鲜被评估。那些空间想象能力相对于其数理和言语推理能力尤为出众的学生,尤其可能得不到我们现有教育体系的充分支持。本文回顾了证明评估空间能力重要性的相关证据,并提出了在学习和工作环境中利用这一能力个体差异信息的方法。本文所回顾的文献强调了空间能力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这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罕见的、无需再进行更多研究来证明的案例。当前需要的,是将空间能力纳入人才识别流程以及课程开发与培训的研究中,并与其他那些对衡量超越智商(或称 g,即一般智力)的社会价值成果具有差异性和增量有效性的认知能力一同考量。
Kell 等人 2013a
「谁能脱颖而出?早期指标的启示」, Kell 等人 2013a:
本研究对 320 名在 13 岁前被识别出具有卓越数学或言语推理能力(顶尖万分之一)的青少年进行了近三十年的追踪。他们截至 38 岁时获得的奖项和创造性成就,结合其职业职责的具体信息,清晰地展示了他们贡献的份量和专业地位。许多人被赋予了重大责任和资源,为个人和组织的福祉做出关键决策。他们在商界、医疗、法律、学术界以及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领导地位表明,其中许多人是现代文化的杰出创造者,是宝贵的人力资本资源。要识别出真正具有深厚潜力的人才,并预测这类人群内部的差异化发展,需要评估多种认知能力并采用非典型的测评方法。本研究展示了如何通过整合及纵向追踪最终成就这些标准,来验证此类测评方法的有效性。
Kell 等人 2013b
「创造力与技术创新:空间能力的独特角色」, Kell 等人 2013b:
20 世纪 70 年代末,563 名智力超常的 13 岁青少年(经 SAT 考试认定为能力排名前 0.5%)接受了空间能力评估。三十多年后,本研究旨在探究空间能力是否在差异化预测这群人中谁获得了专利、谁发表了三类不同级别的同行评审论文方面,提供了超越 SAT 数学和言语推理子测试的增量预测效度。一项两步判别函数分析显示,SAT 的两个子测试共同解释了这些成就差异中 10.8% 的方差(p < 0.01);当加入空间能力这一变量后,额外解释了 7.6% 的方差——这一增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 < 0.01)。这些发现表明,在创造力的发展过程中,空间能力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其作用超越了传统教育选拔、职业咨询及工业组织心理学所测量的能力。空间能力在构建许多重要的心理现象中起着关键而独特的作用,应当在应用和基础心理科学领域得到更广泛的研究。
Park 等人 2013
「当少即是多:跳级对数学早慧青少年成年后 STEM 领域生产力的影响」, Park 等人 2013:
作者们利用一项长达 40 年的纵向研究数据,检验了三个关于跳级对未来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教育及职业成就影响的相关假说。研究从一个包含 3,467 名数学早慧学生(能力排名前 1%)的合并样本中,通过精确匹配和倾向得分匹配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由 363 名跳级者和 657 名匹配对照者组成的平衡比较组。结果表明,跳级者(a)更可能在 STEM 领域攻读高等学位并发表同行评审的 STEM 论文;(b)他们获得学位和发表首篇论文的时间更早;(c)截至 50 岁时,他们积累了更多的论文总引用量和高被引论文。这些规律在男性参与者中表现一致,但在女性参与者中则不那么明显(她们更倾向于在医学或法律领域攻读高等学位)。研究结果提示,跳级可能有助于提升数学天才在 STEM 领域的成就。
《自然》 2013
「中国项目探秘天才基因:揭示智力之谜的尝试面临质疑」,Ed Yong,2013-05-14
20 世纪 70 年代,一群美国青少年加入了「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数学和言语推理能力均位列人群前 1%。如今,坐落于中国深圳、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华大基因(BGI,前身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探寻可能造就这些天赋的 DNA 特征。他们涉足的是一个失败案例累累、争议不断的领域,通过筛查这 1600 名天之骄子的基因组,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首次发现与人类智力相关的常见遗传变异。
……此后,Plomin 调整了策略,只专注于最顶尖的头脑。他从 SMPY 项目的 2000 名参与者中收集了 DNA 样本,这些人的平均智商超过 150——超越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水平,比普通人群 100 分的均值高出三个标准差。「在早前的研究里,我敢说智商这么高的人我们顶多也就有两三个」,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便研究智力遗传性的 Plomin 说道。
……后来,他 [Steve Hsu] 听说了 Plomin 的样本。两人随即展开合作:Plomin 提供了 1600 名 SMPY 参与者的 DNA 样本,Hsu 则补充了他通过自己网站招募的 500 多人的样本——尽管后者的筛选标准没有那么严格……
[此处的摘要似乎有误。Plomin 的这项研究最终以 Spain 等人 2016 的名义发表(据传华大基因的研究因内部混乱而至今未发表);如前所述,研究并未发现能导致智力大幅提升的特殊罕见突变,尽管这种极端案例对照的设计在样本量(n)如此小的情况下确实能提供较高的统计功效。然而,Spain 等人 2016 的论文明确指出,其高智商样本来自杜克大学天才识别项目(Duke TIP),尽管此文声称样本源于 SMPY。
我曾与一位 SMPY 参与者交流,他回忆不起 2013 年前后有过任何招募活动。而 Steve Hsu 在 2014 年的白皮书中将该队列描述为「一些天才项目的校友,这些项目类似于 SMPY,其成员在 13 岁前测试成绩达到万分之一的水平(DNA 样本由伦敦国王学院著名行为遗传学家 Robert Plomin 利用邓普顿基金会的资金获得)」(黑体为译者所加)。我于 2018 年 9 月就此出入询问了 Steve Hsu,他认为「文中所提的 2000 个 SMPY 样本,实际上是指 TIP 项目的样本」,所以大概是他当时口误了,或者可能是 Yong 误解了将 TIP 样本与 SMPY 进行比较的说法。]
Stumpf 等人 2013
「引入空间能力测评,拓展人才搜寻维度:CTY 的空间能力成套测验」, Stumpf 等人 2013:
空间能力对于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已是学界共识。然而,拥有高空间能力的学生却鲜被发掘,因为针对学术天才的「天才搜寻计划」主要聚焦于识别顶尖的数学和言语能力。结果,那些空间能力出众但数学或言语能力并非顶尖的学生,可能因此错失机会。为了识别具有空间天赋的学生,天才儿童中心(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开发了一套「空间能力成套测验」(Spatial Test Battery),作为其数学和言语「天才搜寻计划」的补充。本文追溯了该测验的开发历程,介绍了其构成部分、重要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及后续发展,并鼓励对培养空间天赋感兴趣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使用它。
Beattie 2014
「数学早慧青年研究」, Beattie 2014;该词条收录于《特殊教育百科全书:为残障及其他特殊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提供教育的参考资料》 (ISBN 9781118660584)
Brody & Muratori 2014
「提前入读大学:学业、社交与情感因素的考量」, Brody & Muratori 2014 (出自《一个国家被赋能:证据胜于雄辩,驳斥阻碍美国顶尖学生发展的借口,第 2 卷》,Assouline 等人编,2014):
作为当今众多学业加速选项之一,提前入读大学为那些心智早已准备好迎接大学挑战的年轻学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他们的教育轨迹能比多数同龄人提前一两年,甚至更早。在渴望更大挑战的高中生中,提前入读大学已日益普遍,美国各类提前入学项目的激增便是明证。本章节将回顾提前入读大学的历史,并介绍当今正在实施的各种项目模式。文中亦将呈现相关研究结果,重点突出提前入学者的学业与社会情感发展成果,并探讨这些研究对教育工作者的启示。
Lubinski 等人 2014
「数学早慧男女四十年后的人生轨迹与成就」, Lubinski 等人 2014:
上世纪 70 年代(1972-1974 年和 1976-1978 年),两批智力超常的 13 岁青少年被识别为数学推理能力位列顶尖 1%(共 1037 名男性,613 名女性)。约四十年后,我们收集了关于他们职业生涯、个人成就、心理幸福感、家庭状况以及生活方式偏好与优先级的数据。他们的成就远超普遍预期:综合两批参与者,4.1% 的人在顶尖研究型大学获得终身教职,2.3% 成为「知名」或财富 500 强企业的高管,2.4% 在大型律师事务所或机构担任律师;参与者们共出版了 85 本专著和 7572 篇同行评审论文,获得了 681 项专利,并争取到总额达 3.58 亿 [2014年币值;折合 2025 年为 5.28 亿] 美元的研究经费。无论男女,年少时的数学天赋都预示着其成年后在关键职业岗位上的创造性贡献和领导才能。平均而言,男性的收入远高于其配偶,而女性的收入则略低于其配偶。在生活方式偏好、优先级排序及时间分配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些差异与男女参与者不同的职业发展结果相呼应。
《波士顿环球报》 2014
「可怜的、被忽视的天才儿童:早慧儿童似乎确实成长为高成就的成年人。为何这反而让一些教育家为美国的未来担忧」:
[本文讨论了 SMPY 项目及 Lubinski 等人 2014 年的研究,重点关注当前的筛选机制如何仍会错失天才儿童,以及天才教育普遍被忽视的现状。]
Kell & Lubinski 2014
「成年之际的数学早慧青年研究:洞悉天才的构成要素」, Kell & Lubinski 2014,收录于《威利天才手册》(The Wiley Handbook of Genius),Simonton 编,2014 (ISBN 9781118367377)[4]:
「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始于 1971 年,旨在识别并培养智力早慧的青少年。SMPY 项目五个批次中,最年长的一批参与者如今已年届五十出头。本章节回顾了基于 SMPY 目前追踪的 5000 多名参与者的纵向研究发现,旨在探明智力早慧可能展现的多种不同发展路径,评估教育干预是否有效,并分析那些最终功成名就者与未然者之间的个人特质差异。文中提出了一个才能发展模型,该模型整合了达成卓越成就所必需的关键认知、情感和意动(conative)决定因素。我们描述这些特质,是为了识别那些有望做出杰出创造性成就的潜力人群,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深入理解那些接近甚至可称之为「天才」水平的卓越表现是如何发展的。
Wai 2014a
「专家七分天生,三分培养:结合前瞻性与回顾性纵向数据,揭示认知能力的关键作用」, Wai 2014a:
在教育和职业领域,认知能力对专业技能的发展是否至关重要?研究一回顾了两批「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总 N = 1975)项目中能力位列顶尖 1% 的人群的前瞻性纵向数据,并考察了「天才计划」(Project Talent;总 N = 1536)中四个批次的美国人口分层随机样本,以探究年轻时的能力差异是否影响日后获得更高比例的教育学位,特别是博士学位(如法学博士、医学博士或哲学博士)。与普通人群相比,能力顶尖 1% 的群体在各个学历层次获得的学位比例都高得多。即便在顶尖 1% 的群体内部,能力差异也对能否获得博士学位有影响。研究二回顾了美国五大精英群体(总 N = 2254)——财富 500 强 CEO、联邦法官、亿万富翁、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回顾性纵向数据,以确定各群体中有多大比例的人在年轻时就具备顶尖 1% 的综合能力。研究发现,在上述各个职业精英领域中,都有相当大比例的个体属于能力顶尖 1% 的人群。综合运用前瞻性与回顾性纵向研究的多个样本数据,我们发现,认知能力在获取教育和职业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Wai 2014b
「教育加速的长期效应」, Wai 2014b (出自《一个国家被赋能:证据胜于雄辩,驳斥阻碍美国顶尖学生发展的借口,第 2 卷》;注意勿与 Lubinski 2004b 在该书 2004 年的前作《一个国家被蒙蔽》中的同名论文混淆):
教育干预的形式多种多样。教育加速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它构成了适合个体的「教育剂量」的一部分。「剂量」一词意味着,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单一的干预措施或许不如多种教育干预的正确组合、数量和强度来得有效。本章节回顾了「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的发现,这是一项对数千名智力超常学生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纵向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学业优异的参与者对教育加速的长期教育-职业影响及其主观感受均持积极态度,这证明了教育加速乃至更广义的「适当教育剂量」的重要性。纵向研究的发现揭示,一个旨在让学生以与其学习速率相匹配的节奏前进的教育计划,在教育学上是恰当且必要的。天赋异禀的学生能从加速学习机会中获益,他们对自己曾接受的加速教育几乎无怨无悔,并最终展现出卓越的成就。对每个学生而言,关键在于在漫长的时间里获得持续且充足的「教育剂量」——我们称之为终身学习,即以匹配学生个人需求的速度和强度进行学习。所有学生都应享有每日求知的权利,如果学业天才渴望并准备好接受加速教育,那么长期证据明确支持这种干预措施。
Brody 2015
「Julian C. Stanley 杰出才能研究:满足高能力学生需求的个性化方案」, Brody 2015 (注:原文为西班牙语):
为普通学生设计的常规学校课程,以及那些未能顾及天才学生独有特质的资优项目,都无法满足大多数高阶学习者的学业和个人需求。在为他们制定具有适当挑战性的个人化方案时,应综合考虑每个学生的特定能力模式、学业水平、兴趣、动机及其他个人特质,并结合校内外丰富多样的教育策略与项目。教学的水平和节奏应按需调整,学生应有机会深入探究感兴趣的课题,还应为他们创造机会,与志趣相投、能力相当的同伴交流。这种满足超常学生学业与社会心理需求的个性化方法,早已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杰出才能研究」(SET)项目及其前身「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的同仁们成功运用。如今,随着社会对个性化学习的兴趣重燃,我们有机会将此方法更广泛地制度化。然而,这需要学生能从知识渊博的成年人那里获得关于发展其才能的课程信息和建议;学校必须保持灵活性,愿意调整课程并认可校外学习成果;同时,也必须解决可能限制学生参与校外项目的经济壁垒。
此外,科学的评估,尤其是「超纲」评估,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决策。这类评估能够区分不同层次的天才学生——有些学生只需富有挑战性的同年级课程即可,而另一些则需要接触更高年级的内容。本文介绍了 SET 项目在为其服务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经历时所采用的方法,希望能为他人提供借鉴。
Lubinski 2016
「从 Terman 到今天:百年智力早慧研究的回顾与启示」, Lubinski 2016:
本文回顾了过去一百年(1916-2016)间关于智力早慧青年的研究,描绘了一幅关于这一非凡人力资本源泉的图景,并探讨了促进其取得卓越成就、获得生活满足感和实现积极成长所需的学习机会。研究焦点集中于那些针对综合能力或专项能力(数学、空间或言语推理)位列顶尖 1% 的个体所进行的研究。早期对天才现象的洞见,实际上已预示了百年后将被科学证实的结论。因此,基于证据的观念迅速转变,不再将智力早慧者视为体弱多病、情绪不稳的群体,而是看作高效且富有韧性的个体。与所有群体一样,智力早慧的学生和成年人也有其长处和相对的短板;他们对于不同事业的热情和追求卓越的动力也千差万别。由于他们并非全能,我们必须从多维度的视角来审视他们的个体特质。当我们这样做时,便能很好地预测其长期的教育、职业和创造性成果。
《自然》 2016
「如何培养天才:一项长达 45 年的超常儿童研究带来的启示——对杰出儿童的长期追踪,揭示了培养引领 21 世纪的科学家所需的条件」, Clynes 2016:
1968 年的一个夏日,Julian Stanley 教授遇到了一位名叫 Joseph Bates 的 12 岁少年,他才华横溢却深感课堂枯燥。这位巴尔的摩的学生在数学方面遥遥领先于同班同学,他的父母便安排他在 Stanley 执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修读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即便如此,挑战性仍显不足。这个孩子在课堂上迅速超越了成年学员,并开始给研究生们教授 FORTRAN 编程语言以打发时间……Bates 的测试成绩远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录取标准,这促使 Stanley 开始寻找愿意让这个孩子修读高等数学和科学课程的本地高中。当这个计划失败后,Stanley 说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学院院长,让时年 13 岁的 Bates 以本科生身份入学。
Stanley 后来亲切地称 Bates 为他的「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的「零号学生」。这项研究后来彻底改变了美国教育系统识别和支持天才儿童的方式。作为目前仍在进行的、针对智力超常儿童的最长期的纵向调查,SMPY 在过去 45 年里,持续追踪了约 5000 名个体的职业生涯与成就,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成就斐然的科学家。该研究不断扩充的数据库催生了 400 多篇论文和数本专著,为如何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及其他领域发现和培养人才提供了关键的洞见……
Makel 等人 2016
「当闪电两次击中:天赋异禀,成就非凡」, Makel 等人 2016
「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中那些极具天赋(智商 > 160)的参与者所取得的教育、职业和创造性成就令人惊叹,但他们的经历是否能代表其他同等能力的 12 岁少年?杜克大学的「天才识别项目」(TIP)曾识别出 259 名同样天赋异禀的青少年。到 40 岁时,他们的人生同样成就非凡:37% 的人获得了博士学位,7.5% 的人获得了终身教职(其中 4.3% 在研究密集型大学),9% 的人拥有专利;许多人已是大型组织的高层领导。与他们之前的 SMPY 样本一样,他们各异的能力优势预示了他们迥然不同且最终成型的成长轨迹——尽管几乎所有参与者的数学和言语推理能力都远超典型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即便是天赋异禀的个体,也主要从事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能力模式的差异,如同兴趣的差异,引导着个体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而能力水平,加上不懈的努力,则决定了在机遇来临时,他们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瞩目的成就。
图 1. 两个样本在 13 岁时的 SAT-数学与 SAT-言语分数散点图:杜克大学「天才识别项目」参与者(上图)与「数学早慧青年研究」参与者(下图)。每张散点图中的对角线标示了估算智商为 160 的分界线(据 Frey & Detterman, 2004; Lubinski, Webb, Morelock, & Benbow, 2001, p. 719);位于对角线上方的双变量数值对应于估算智商高于 160 的个体。坐标轴上的粗体数字分别表示该年龄段能力排名前 1/200 和前 1/10000 的分数线。
表 3. 杜克大学「天才识别项目」参与者创造性成就详情(N = 259)
表 4. 杜克大学「天才识别项目」参与者的职位头衔及其任职机构描述
表 5. 「天才识别项目」参与者获得终身教职的机构及其发表作品的同行评审期刊
Spain 等人 2016
「与极高智力相关的推定功能性及外显子变异的全基因组分析」, Spain 等人 2016:
尽管智力(一般认知能力)的个体差异具有高度遗传性,但迄今为止的分子遗传学分析在识别其遗传性的特定基因位点方面收效甚微。本研究首次对极高智力个体的外显子组变异进行了调查。根据数量遗传学模型,从分布的极端高值端取样理应能提高检测到关联性的统计功效。因此,我们进行了一项病例-对照关联分析,样本包括 1409 名从智力分布顶端 0.0003(智商 >170)挑选的个体,以及 3253 名未经筛选的普通人群对照组。我们的分析聚焦于通过 Illumina HumanExome BeadChip 芯片检测出的推定功能性外显子变异。我们未能观察到任何单一的、可被重复验证的、与极高智力乃至整个智力分布相关的蛋白质改变变异。此外,也未发现单个基因内的多个罕见等位基因存在显著关联。然而,采用非亲缘个体间全基因组相似性分析方法(全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易感性阈值模型,已测序的功能性蛋白质改变变异能够解释 17.4%(标准误 1.7%)的遗传度。此外,对名义上显著的关联进行调查后发现,与极高智力相关的罕见等位基因数量少于零假设下的预期。这一观察结果支持了以下假说:罕见的、具有功能的等位基因对智力而言,更有可能是弊大于利。
……高智力病例组(HiQ):研究对象从杜克大学「天才识别项目」(TIP)中招募。该项目是一个成立于 1980 年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有学术天赋的儿童35(详见 Tip.duke.edu)。参与 HiQ 研究的个体是从全美范围内选拔的,其依据是他们在 12 岁(而非通常的 18 岁)时参加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或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的成绩。综合 SAT 和 ACT 的言语与数学分数所得的复合分,与智力测验得分的相关性超过 0.80,据此估计,TIP 项目招募的学生来自智力分布的前 3%。36
Kell 等人 2017
「天才儿童与高成就者健康状况良好:四个SMPY队列50岁时的健康状况」,Kell 等人 2017 (会议摘要)
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业已证明,智力与良好的健康状况正相关(Terman, 1925, 《千名天才儿童的身心特质》)。尽管如此,一些人仍质疑天才儿童长大后(平均而言)能否成为身心健康、社会适应良好的成年人(如 Neihart, 1999)。本研究将普通人群(n = 3,652)中的中年人与四个「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队列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比较。队列1(n = 1,159)的能力水平位列前1%,队列2(n = 491)则位列前0.5%。在被识别四十年后,这两个队列的成员均参与了一项全面的生平调查,其中包含诸多健康问题(Lubinski, Benbow, & Kell, 2014)。在全部23个项目中,天才男性在其中22项(96%)上表现出比普通智力水平的男性更为积极的健康状况。其平均比值比(OR)为5.32,这意味着普通智力水平的男性遭遇负面健康问题的几率是智力顶尖1%男性的五倍以上。天才女性则在65%的类别中表现出更积极的状况,平均比值比为2.52。
由于队列1的平均年龄(53岁)高于队列2(48岁),对智力顶尖1%人群内部的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变得更为复杂。天才女性之间仅出现了两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与智力顶尖0.5%的女性相比,顶尖1%的女性更可能感到内心平静祥和,且近期更少因情绪或生理问题影响日常活动(平均 d = 0.12)。男性的结果则不尽相同。智力顶尖1%的男性在统计上更有可能出现胸痛、高血压和关节炎(OR = 2.23),而顶尖0.5%的男性则更有可能患有哮喘、抑郁症及其他非抑郁性精神疾病(OR = 1.2)。
作为一项重复研究,我们对另外两个SMPY样本进行了同样的调查。队列3由1980年代初被识别为智力水平位列前0.01%的青少年构成(预期样本量 n > 300)。队列4由1992年在美国排名前15的数学/科学研究生项目就读的一、二年级学生构成(预期样本量 n > 400)。这两个新队列的健康状况不仅将与普通人群进行比较,还将与智力顶尖1%和0.5%的群体进行比较。这些数据的规模、广度和质量为我们审视智力超群的成年人的幸福状况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最后,这些数据还让我们得以比较三组在青少年时期即被识别为高能力群体与另一组在成年早期被公认为卓越成就者的人群之间的健康状况。注:队列3和队列4的初步数据尚待分析,但调查工作已在顺利推进。初步研究结果将于2017年在国际智力研究学会(ISIR)年会上首次公布。
Wai & Kell 2017
「我们已经错失了哪些创新?:识别与培养空间天赋的重要性」,Wai & Kell 2017:
在刘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一项著名的人才筛选研究中,有两位男孩未被识别为天才,但他们后来都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是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而他们声名鹊起的科学领域在本质上可以说高度依赖视觉空间能力。为何两位诺奖得主会被遗漏?很可能是因为特尔曼采用了高度侧重语言能力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该量表并未包含对空间能力的有效测量。如今,学校中的许多标准化考试都缺乏对空间能力的测量,这意味着大量具备空间天赋的学生未被识别,其天赋也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培养。本章首先回顾了五十余年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空间能力同数学和语言能力一样,在STEM领域具有预测价值。其次,本章讨论了空间能力训练以及女性在STEM领域的议题。再次,本章阐述了如何将这些研究发现及其他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最后,本章将探讨忽视空间天赋学生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譬如,正是因为我们未能充分识别和培养一些最具潜力的创新者的天赋,我们究竟已经错失了多少创新成果?
Lubinski 2018
「顶尖群体的个体差异:绘制智力范围的外层包络」,David Lubinski (收录于《人类智力的本质》,Sternberg主编,2018年,ISBN 1316819566)
Bernstein 等人 2019
「13岁时评估的心理特质组合可预测35年后不同形式的卓越成就」,Brian O. Bernstein、David Lubinski、Camilla P. Benbow 2019 (SMPY,科学;反向链接,相似):
本研究旨在检验,当初为预测智力超常的13岁青少年在23岁时的学业发展而建立的数学/科学和语言/人文领域的能力与偏好组合模型,在35年后是否依然具有长期的预测效力,能够区分出不同形式的卓越成就。卓越人士被定义为在50岁前取得稀有成就的个体:其职业生涯富有创造性且影响巨大(例如,研究密集型大学的正教授、《财富》500强企业高管、知名法官与律师、生物医药领域领袖、获奖记者与作家)。
研究1 的对象为677名智力早慧的青少年,他们在13岁时接受评估,并在35年后对其领导力与创造性成就进行评估。研究2 则构成了一项建构性复制——对605名顶尖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的研究生进行分析,他们在研究生初期接受了基于相同预测构念的评估,并在25年后再次接受评估。
在两个样本中,用于界定数学/科学型与语言/人文型特质组合的同组能力与偏好参数,成功地区分了日后取得不同形式卓越成就的参与者和那些追求其他人生目标的同龄人。
表1:研究1结果: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他领域被归为卓越的参与者描述性统计(n = 83)。
注:R1 = 研究密集型大学;NIH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SF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a) STEM领域的例外是一位在小型荣誉工程学院任教的教授,他同时是美国一所顶尖STEM大学的访问学者。此人著有多本STEM书籍,在网络STEM教育领域声名卓著。(b) 人文科学领域的例外是一位在非研究密集型学院任教的教授,其发表记录与人文/社会科学组的其他成员相当。
表2. 研究2结果: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被归为卓越的参与者描述性统计(n = 124)。
注:若个体满足多项标准(例如,既是发表论文75篇以上的正教授,又获得至少275万美元 [2019年币值;相当于2025年的350万美元] 政府资助),则在每个达标类别中均被计数。R1 = 研究密集型大学;NIH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SF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a) “其他”组包括不符合此6项标准的STEM领袖。其中包括一名宇航员、一名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多篇论文且获非政府资助逾300万美元 [2019年币值;相当于2025年的381万美元] 的研究员、一家承担高影响力政府项目的公司的高级主管、一所高研究活动大学(R2)的正教授(其论文发表和资助总额略低于我们的界定标准),以及一位在国家级研究实验室中发表论文超过60篇的研究主管。
图1:研究1结果:各卓越/领导力类别的数学/科学功能与语言/人文功能的双变量均值。
图中展示了三个主要的卓越类别: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STEM组的一个子集——研究密集型大学(R1s)的正教授——也一并展示。
围绕这些主要质心的是代表两种功能得分的±1倍标准误(SEM)(内部阴影椭圆)和±1倍标准差(SD,外部开放椭圆)的椭圆。样本量在括号内标明。虚线将个体数据点与其所属类别的质心相连。
结构矩阵中的数值代表线性判别函数与源自Achter等人1999年研究的能力和偏好测量值之间的相关性。SOV = 价值观研究。
McCabe 等人 2019
「群英荟萃,谁主沉浮?:一项针对顶尖STEM研究生的25年纵向研究」,McCabe 等人 2019:
1992年,「数学早慧青年研究」(SMPY)项目对714名就读于美国STEM领域排名前15位大学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其中48.5%为女性)进行了调查。本研究旨在探究他们在研究生生涯早期所评估的个体差异,是否与25年后成为STEM领域的领军人物(例如,研究密集型大学的STEM正教授、STEM企业的CEO及政府部门的STEM领导者)有关。我们同时还研究了在STEM领导力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兴趣、价值观和个性方面的中小型效应量差异,都能够区分出STEM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生活方式与工作偏好同样是区分因素:STEM领导者更专注于事业,他们期望并确实投入比非领导者更多的工作时间。此外,在能力、兴趣及生活方式偏好上,也存在着从小到大不等的性别差异。男性对STEM领域兴趣更浓厚,更以事业为中心。女性则拥有更多元的教育与职业兴趣,并对工作之外的活动更感兴趣。因此,即便是在顶尖的STEM研究生群体中,早在研究生初期便有迹象预示谁将成为未来的STEM领导者。鉴于成为STEM领导者的路径多种多样,这一高潜力样本中所揭示的性别差异表明,男性和女性可能会对这些发展机会赋予不同的优先级。
注意,本研究并非直接调查通过SAT-M考试或童年测试招募的SMPY队列,而是对一批作为顶尖大学STEM研究生入组的队列进行的后续调查,相关情况在Lubinski等人2001a中有报告。
Kell & Wai 2019
「右尾范围限制:一个在探究专家特质与技能关系时潜藏的威胁」,Kell & Wai 2019
一些知名学者曾声称,在专家群体中,某些人类特质(如认知能力、体能)的差异与技能水平的差异之间并无关联。我们认为,之所以未能发现此类关联,往往是由于一种极端的范围限制问题,这一问题在针对专家样本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我们称之为「右尾范围限制」(Right-Tail Range Restriction, RTRR)。RTRR指的是在数据中,来自正态分布远右端(即顶尖水平)的样本代表性不足,从而妨碍了统计关联的观测。通过两个案例研究,我们证明了当RTRR问题不存在时,专家特质的差异与其技能水平的差异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基于这些研究的特点,我们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法的建议,以帮助研究人员克服RTRR问题,从而推动专业技能研究这门科学持续发展,使其更为稳健和可复制。[关键词:范围限制,专业技能,特质,认知能力,体能,绩效,体育运动,心理属性]
本文重新分析了Kell 等人 2013、Lubinski & Benbow 2006、Lubinski 等人 2014及Makel 等人 2016的研究。
2020
Bernstein 等人 2020
「天才青少年的学业加速与对心理健康的无谓担忧:一项长达35年的纵向研究」,Bernstein 等人 2020:
人们普遍认为,对智力早慧青少年进行学业加速会有损其整体心理健康,尽管短期研究并不支持此观点。本研究旨在检验其长期影响。研究1涵盖了三个在13岁前被识别并接受了超过35年纵向追踪的队列:队列1为天才组(能力排名前1%,1972-1974年识别,n = 1,020),队列2为高天数组(能力排名前0.5%,1976-1979年识别,n = 396),队列3为极度天才组(能力排名前0.01%,1980-1983年识别,n = 220)。研究考察了两种形式的教育加速:(a) 高中毕业年龄,及(b) 高中毕业前参与的进阶学习机会的数量。参与者在50岁时接受了多项知名心理健康指标的评估。结果显示,学业加速的程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并无相关性。研究2作为研究1的建构性复制,采用了一个不同的高潜力样本——一批于1992年被识别的顶尖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的研究生(n = 478)。研究在他们25岁时评估了其教育经历,并在50岁时采用相同的心理评估进行追踪。结果再次显示,教育加速的程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并无相关性。此外,两项研究中参与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均高于全国概率抽样样本的平均值。因此,对于高潜力学生而言,担心学业加速会带来长期的社交/情感负面影响似乎是多余的,这与短期效应的研究结果相符。[关键词:天才,学业加速,复制,适当发展安置,心理健康]
影响声明:最佳实践表明,多种形式的学业加速是满足智力早慧青少年高阶学习需求的有效教育方法。然而,家长、教师、教育管理者及心理学理论家却担心此举会引发负面的心理效应。一项对三个智力早慧青少年队列长达35年的追踪研究表明,这种担忧并无必要。这些发现在一个顶尖STEM毕业生样本中得到复制,该样本在25岁时评估了其教育经历,并接受了25年的追踪。
Lubinski & Benbow 2020
「智力早慧:自特尔曼时代以来我们学到了什么?」,Lubinski & Benbow 2020 (综述):
在过去五十年间,通过纵向研究,关于智力早慧的八大稳健结论得以提出、实证并复制。在综合能力及专项能力(数学、空间、语言)的顶尖1%群体中,包含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个体差异范围,而这些差异意义重大。能力水平和特定能力模式上的这些个体差异,通过超常水平评估得以揭示,并决定了在教育、职业和创造性产出上重大的量化及质化差异。在预测未来成就方面,能力不存在阈值效应;当评估涵盖全部三种主要能力的完整范围时,所谓“多方面潜能”的概念便不攻自破。在能力之外,教育/职业兴趣对于为早慧青年寻找最优学习环境具有附加价值,若再结合意动变量,则能更好地构建其后续的生涯发展模型。尽管极端早慧的青年其总体职业成就与其能力一样出类拔萃,但足够强度的教育干预能提高他们成就非凡事业、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概率。研究结果清晰地揭示了智力早慧群体内部的心理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也说明了满足他们学习需求所需的环境多样性。将天赋及相应干预措施进行僵化的分类,已经阻碍了该领域的进步。[关键词:基本诠释,混合方法,心理测量学,评估,创造力,天才]
1. 是否存在能力阈值,超过该阈值后,更高能力便不再重要? 否。
2. 特定能力的组合模式是否重要? 是。
3. 是否存在“多方面潜能”的证据? 否。
4. 对于智力天赋尤其卓著的学生,能力模式是否依然重要? 是。
5. 教育/职业兴趣能否为智力早慧青少年的能力评估提供附加价值? 是。
6. 鉴于当前对STEM领域人才资本的识别与培养日益重视,天才研究领域是否有其他重要发现能回应此需求? 是。
7. 教育干预能否提升学习效果与最终的创造力表达水平? 是。
8. 除了能力、兴趣和机遇,意志、动机等意动特质是否重要? 是。
9. 智力早慧研究是否对其母学科——教育学和心理学——做出了贡献?是否存在一个贯穿上述、并被数十年研究反复验证的共通主题? 是的。而且是的。
Henshon 2020
「追求卓越:琳达·布罗迪访谈录」,Henshon 2020:
[对琳达·布罗迪(Linda Brody)的简短访谈。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青少年中心(CTY)“卓越才能研究”(SET)项目的现任主管;她于1970年代开始在SMPY项目与科恩(Cohn)/皮里特(Pyryt)/本博(Benbow)以及林恩·福克斯(Lynn Fox)和朱利安·斯坦利(Julian Stanley)共事,后于1991年转至CTY。她的专业领域是“双重特殊学生”(即既有天赋又身患残疾)。SET项目目前正在对其校友进行研究。]
Schuur 等人 2020
「跳级大学生的社会情感特征与适应性:一项系统性综述」,Schuur 等人 2020 (系统性综述):
在中小学阶段经历过跳级的天才学生,在适应大学生活时面临着比同龄人更早的挑战。本系统性综述旨在严格评估关于这些跳级天才大学生的社会情感特征与适应性的研究。通过对22项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社会情感特征的多个方面,跳级学生与未跳级的天才同伴及非天才同伴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促进其适应与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乐观开朗的性格、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积极的自我概念、优异的过往学业成绩以及支持性的家庭环境。此外,研究发现现有文献在报告学生的过往跳级经历方面不够完整,且针对个人跳级1至2年的学生的研究尤为匮乏。未来的研究应当纳入个人跳级学生、过往跳级经历、性别差异以及对照组。
2022
Kell 等人 2022
「为成功所累?无需过虑」,Kell 等人 2022:
我们检验了「为成功所累」这一假说。该假说最初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现已在人文学科、大众媒体及现代科学文献中广为流传。它认为,真正卓越的职业成功往往会以牺牲心理、人际和生理健康为沉重代价。研究1在三个队列共1,826名高潜力、智力超常的个体中检验了此假说。研究将职业生涯异常成功的参与者与其性别相同、智力水平相当但职业发展较为普通的同伴进行比较,考察了他们在知名心理健康、人生蓬勃度、核心自我评价及生理疾患等方面的指标。家庭关系、对衰老的从容度以及生活满意度也一并纳入评估。结果显示,在所有三个队列中,那些被认为在职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个体,其各项指标与同伴相比,或相差无几,或更为健康。研究2作为研究1的建构性复制,采用了一个不同的高潜力样本:496名于1992年被识别并接受了25年纵向追踪的顶尖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博士生。研究2在所有重要方面均重复了研究1的发现。两项研究均表明,异常成功的职业生涯与生理耗竭、心理失调、人际及家庭关系受损并无关联;相反,总体而言,事业异常成功的人士在身心方面反而更为健康。
参见
其他:
- 「越多是否越差?兴趣过剩与STEM职业中的性别差距」,Cardador 等人 2020
1957
《科学事业与职业发展理论:综述、批判与建议》,Super & Bachrach 1957:
“科学事业项目”专题组就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的特质与动机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体现了对职业发展与选择过程的一种跨学科视角。研究强调了事业与职业之间的区别,以及同一事业内部不同子专业和子类别之间的差异。三种基本理论取向——特质-因素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和人格理论——应当被整合为一个动态的职业模式概念,这一概念在职业发展理论中得以体现,即将职业选择视为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
1964
《空间能力:其教育与社会意义》,Smith 1964;摘自前言:
乍看之下,本书似乎是对某些心理测验统计结果的一份高度技术性的考察报告。但作者在审慎权衡证据后得出的结论,对当前的教育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因此,教育界人士亟需花时间去了解并深思这些技术性证据。简言之,麦克法兰·史密斯(Macfarlane Smith)博士的论点是:英国的教育,尤其是文法学校的教育,在强调发展通用或全面智力的同时,过分看重语言型能力,却牺牲了其在心理学上的对立面——空间能力。克劳瑟报告、查尔斯·斯诺爵士及众多公众人物固然已大力倡导发展数学、技术和科学教育,并指出了英国对技术专家和科学家的需求。然而,这些倡导者中,鲜有人对他们希望鼓励的这些能力的本质、其共通核心,以及这一核心如何与其他能力、气质特征及人格品质相关联有科学的认识。他们或许也未充分意识到,我们现行的中学和大学选拔体系,实际上正在主动地排斥那些最可能在这些方面具备天赋的学生。
麦克法兰·史密斯博士概述了大量关于空间能力、操作能力、机械能力及其他非语言能力的测试研究,并指出这些能力背后存在一个主要的潜在因素或能力类型,其最佳定义是:将一个形状或图形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能感知和在脑海中保持其结构与比例的能力。这一观点调和了英美研究者之间略有分歧的研究结果,因为后者常使用不太恰当的多项选择测验,这类测验更侧重于识别细节,而非感知与重现复杂的整体。大量证据表明,此类测验在技术课程与培训、几何学和艺术领域的选拔中颇为有效。此外,一项对数学能力的全面调查显示,除了通用智力测验(最好是非语言形式的)外,最具预测效力的也是空间因素测验。相比之下,机械的算术测验几乎无法预示未来的数学或科学能力(因此,克劳瑟报告所倡导的“数感”在心理学上是具有误导性的)。似乎对形式的感知是数学与科学所涉抽象思维的一个普遍特征,这与多数学校科目所涉的语言思维截然不同。
本书还综述了大量关于脑损伤、脑瘫和脑白质切断术所导致的空间能力缺陷的有趣研究;对该能力与注意类型(分析型vs综合型)及脑电波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揭示了其背后的神经与心理过程。最后,作者有力地论证了空间能力与内向、男性化及主动性等气质品质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隔阂,其根源或许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与其完整的人格构造紧密相连。
1985
「视觉思维:想象现实的艺术」,Root-Bernstein 1985:
[本文探讨了视觉空间推理能力/空间能力/“想象力”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文章以雅各布斯·亨里克斯·范托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为例展开,范托夫是科学可视化方法的倡导者,他通过将“原子”概念进行字面化的几何想象,预测了四面体碳结构。Root-Bernstein继而讨论了他本人对杰出科学家的传记研究,发现他们往往在绘画等其他领域或爱好中也极富创造力,并列举了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和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等例证,他们在成为伟大发明家或科学家之前曾是画家——这类训练可能直接有助于他们精细观察样本并以素描形式重现。Root-Bernstein总结道:
1. 与语言推理相比,视觉推理的价值可能被严重低估,因为“多数人似乎将语言思维视为最高级甚至唯一的思维形式”。
2. 科学哲学或形式逻辑难以对科学思想的起源(而非其表达或验证方式)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解释,其根源可能就在于对语言形式主义的过度依赖;视觉方法或能揭示科学创造的真正逻辑。
3.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可能与此相关。
4. 依据第1点,当前的教育可能正在严重损害学生的科学能力:“完全依赖书本知识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奥斯特瓦尔德、麦克斯韦和吉布斯通过绘画、雕塑、发明和制作等爱好探索自然,他们从中获取的知识无疑与(甚至超过)正规的书本学习。再回到欣德尔对莫尔斯和富尔顿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发明家型科学家的非语言技能,最好通过积极参与艺术活动来激发。然而,在美国许多高中和大学,理科专业的学生却被明确劝阻参与艺术项目,因为艺术和手工技能被认为不具备智力价值。”]
参见:
- 「通过可视化实现科学创造」,Walkup 1965
- 《视觉思维》,Arnheim 1969;「为视觉思维辩护」,Arnheim 1980
1986
「数学天才学生的识别与培养:一项试点研究的理论基础」,Wagner & Zimmerman 1986:
在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中,我们每年为十二岁的、具备高度能力和动机的学生举办数学人才选拔。其中,150名学生参与了一个长期的周六增益课程,旨在训练他们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的数学能力。本文首先探讨了天才儿童教育项目在教育和组织层面所受的限制。我们将数学天赋定义为在两项测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学术能力测验数学部分(SAT-M)和HTMB,后者是专为此次人才选拔设计的包含七个问题的一套试题。文中通过实例阐释并说明了教学项目的理念。初步结果显示该项目取得了显著成功,并指出了其对常规课堂教学可能带来的启示。
安妮·罗 (Anne Roe)
[最早一批直接针对]高智商研究人员的研究是由安妮·罗(Anne Roe)实施的。她与SMPY项目使用SAT考试类似,采用了特别设计的标准化测试题目以避免天花板效应,从而能够恰当地测量其精英研究对象(通常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认知能力。尽管罗的研究更侧重于人格/精神病学而非心理测量学,其研究结果与SMPY的发现大体相似。
富勒顿纵向研究 (Fullerton Longitudinal Study)
以下是从FLS项目中摘选的,关于「智力与动机双重天赋」主题的部分论文:
- 《天才的智商:早期发展层面:富勒顿纵向研究》,Gottfried 等人 1994
- 「智力超常儿童的学业内在动机纵向研究: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Gottfried & Gottfried 1996:
本研究在富勒顿纵向研究的框架下,考察了智力超常儿童及一个对照组的学业内在动机。研究在儿童9岁至13岁期间,采用「儿童学业内在动机量表」对他们进行评估,该量表测量儿童在阅读、数学、社会研究、科学等学科以及对学校整体的内在学习动机。分析表明,在所有年龄段,与同龄对照组相比,天才儿童在所有学科领域及学校整体上均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学业内在动机。研究认为:日后成为智力超常的儿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学习过程;内在动机对于激发天赋至关重要;在选拔学生参加天才项目时,应将学业内在动机的评估纳入考量。 - 「迈向天才动机的概念化发展」,Gottfried & Gottfried 2004:
尽管已有观点将动机视为与天赋相关的一个构念,但我们提出的概念化框架主张一个新视角:动机本身即是一个天赋领域。学业内在动机(即享受学校学习的乐趣)是此概念化框架的核心,因为它与认知、超常智力及成就存在内在关联。以下几点获研究支持,可作为发展天才动机构念的初步标准:(a) 与对照组相比,智力超常者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学业内在动机;(b) 在控制了智商影响后,学业内在动机与学业成就依然存在显著、正向且独特的关联;(c) 学业内在动机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表现出高度的连续性;(d) 环境与学业内在动机显著相关。天才动机这一构念不仅为后续探究提供了启发,也对天才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具有指导意义。文中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天才动机构念所需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 「高动机天赋青少年的教育特征:一项从入学到成年早期的纵向调查」,Gottfried 等人 2005:
本研究在一项当代的长期纵向调查中,检验了“天才动机”这一构念。我们将学业内在动机极高的青少年(即具有天才动机者)与同龄对照组进行比较,考察了他们从小学到成年早期在多项教育相关指标上的表现。学业内在动机的评估基于「儿童学业内在动机量表」。跨时间、普遍性的差异持续显现,高动机天赋组在动机、成就、课堂表现、智力水平、自我概念及高等教育进展上均优于对照组。这些差异具有显著的效应量,并得到了教师观察的佐证。“天才动机”被证明是独立于“天才智力”的。本研究拓展了“天赋”的定义,将“天才动机”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天赋构念。这些发现对于识别具有天才动机的学生并将其纳入天才项目具有重要启示。 - 「富勒顿纵向研究:一项针对智力与动机天赋的长期调查」,Gottfried 等人 2006:
富勒顿纵向研究是一项历时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当代前瞻性调查。研究从儿童1岁时开始,对[n = 130]名儿童及其家庭进行系统追踪,婴儿期至学龄前每6个月一次,5至17岁每年一次,并在24岁时再次进行评估。研究在学业、认知、自我认知、气质、行为、社交、家庭/环境过程及成年期教育成就等广阔的发展领域内,考察了智力天赋 [IQ>130, n = 20] 和动机天赋 [基于“儿童学业内在动机量表”(CAIMI); n = 21] 儿童的发展轨迹。本文介绍了该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对天赋研究的独特贡献,并呈现了关于这两个不同天赋维度的主要发现,同时探讨了其对教育实践的启示及未来研究方向。 - 「关于智力天赋早期预测与识别的若干问题」,Gottfried 等人 2009:
本章包含三部分:(a) 对Colombo、Shaddy、Blaga、Anderson和Kannass所著章节「婴幼儿期的高认知能力」(见本书第2章)的评述;(b) 对天才智力早期预测相关问题(特别是信度/重测稳定性)的探讨;以及(c) 对智力天赋早期识别所涉问题的讨论。 - 「天才动机的发展:纵向研究与应用」,Gottfried & Gottfried 2009:
Gottfried & Gottfried (2004) 提出,“天才动机”是独立于智力天赋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天赋领域。天才动机适用于那些在某项事业中表现出卓越追求与决心的个体。这一构念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均基于作者们在学业内在动机领域所做的天赋纵向研究。学业内在动机被定义为享受学校学习的乐趣,其特征在于追求精通、好奇心、毅力、任务内源性,以及乐于挑战高难度、新颖的任务。本章将介绍天才动机的理论与最新研究发现,并探讨其与从童年到成年早期的即时及长远发展成果的关系。文中还将提出关于天才动机的识别、项目选拔以及项目开发与评估的建议。 - 「发展才能:一项关于智力能力与学业成就的纵向调查」,McCoach 等人 2017:
富勒顿纵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构建从小学到中学阶段智力与学业成就的稳定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模型。我们采用潜变量建模方法,拟合了一个交叉滞后面板模型,以检验智力与数学、阅读两个学科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学业成就在整个学生时代都高度稳定。童年时期的智力是预测初始数学和阅读成绩的强有力指标。然而,在7岁以后,一旦将先前的学业成就纳入考量,智力便不再能预测数学或阅读的后续成就。这意味着,入学时学业基础扎实的学生,往往在整个中小学阶段都能保持其学业优势。我们讨论了这些结果对于才能发展的启示。
慕尼黑研究
慕尼黑 1990
- 「西德慕尼黑纵向天赋研究:目标、方法与初步成果」,Heller 1990 (收录于 Taylor 主编,1990, 《拓展全球创造潜能意识》)
- 「天赋的本质与发展:一项纵向研究」,Heller 1991:
本文在简要探讨天赋的概念与理论问题后,介绍了一项(截至当时)为期四年的纵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及部分成果。该研究基于一个多维度的天赋概念,涵盖:智力、创造力、社交能力、音乐能力、心理能力(或称实践智力)。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学业成就与休闲活动,还涉及与天赋相关的认知与动机人格因素,以及学校和家庭的社会化环境。在项目第二阶段,研究核心转向了对6至18岁的天才学生与普通学生在发展与成就方面的分析。最后,文章探讨了在识别天才儿童与青少年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对天赋培养的启示。 - 「慕尼黑纵向天赋研究的部分成果:多维度/类型学天赋模型」,Perleth 等人 1993:
慕尼黑纵向天赋研究(1985-1989年进行)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天赋研究,它在三个时间点对六个不同年龄的队列进行了测量。本文旨在阐释该研究中多维度、类型学的天赋观。在简要概述后,文章呈现了验证多维度天赋模型及建立天赋类型学的研究成果。结果表明,多维度模型能有效预测成就行为,但建立天赋类型学的尝试并未成功。最后,研究证明,智力型天才与创造型天才在成就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还探讨了这些发现对于在学校中培养天才,尤其是创造型人才的启示。 - 「慕尼黑纵向天赋研究」,Perleth & Heller 1994 (收录于《超越特尔曼:当代天赋与才能纵向研究》)
慕尼黑 2000
- 「天才与才华出众学生的识别」,Heller 2004:
本文以四个与识别天才学生相关的主要问题作为引言,随后重点探讨以下议题:(1) 将多维度天赋观作为构建恰当识别程序的前提;(2) 识别措施的功能、益处及其潜在风险;(3) 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以及(4) 为识别不同类型的天才学生提出的实践建议。 - 「旨在识别与培养天才学生的慕尼黑天赋模型」,Heller 等人 2005:
决定天才教育成效的关键,在于个体在发展与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及非认知因素(如动机及其他人格特质),与主要源自家庭、学校和同伴等社会环境影响之间的匹配程度。本章内容基于多维度的天赋与才能观念,如「慕尼黑天赋模型」(MMG),以及交互作用模型,如Cronbach & Snow (1977) 和Corno & Snow (1986) 提出的「性向-处遇交互作用」(ATI)模型。
当我们将MMG视为一个多因素天赋概念的范例,并结合近期发展的动态过程模型——「慕尼黑动态能力-成就天赋模型」(MDAAM)时,便会引出以下问题:应当如何识别和教导天才个体?又该如何评估他们的学习成果或卓越表现?本文将依据MMG和MDAAM对这些及其他相关问题作出解答。 - 「慕尼黑高能力成套测验(MHBT):一种多维度、多方法的评估路径」,Heller & Perleth 2008:
本文在简要引言之后,第一部分将概述「慕尼黑高能力成套测验」(MHBT)的理论基础。MHBT是在慕尼黑纵向天赋与才能研究的框架下开发的。它不仅包含了测量智力、创造力、社交能力等多个天赋维度和类型的认知预测指标,也包含了与天赋相关的非认知人格与社会调节变量,如兴趣、动机、学习情绪、自我概念,以及家庭和学校氛围、教育方式、教学质量等。文中将详细介绍MHBT的各项工具(不同的量表和维度)。
文章第二部分,在论述了MHBT的客观性、信度和效度之后,作者们将讨论其标准化程序,包括建立基于年级的T-常模,以及构建多种才能剖面图,例如:高成就天才与低成就天才的对比、智力型/创造型/社交型才能的剖面,以及语言/数学/科学才能的剖面等。最后,文章将通过基于 MHBT 的天才项目人才选拔实例和案例研究,来阐释多维度识别程序的应用。
MHBT满足了天才教育与咨询实践中最核心的评估需求。在过去十年中,MHBT 在天赋研究及天才项目评估中的有效性也已得到证实。因此,MHBT为评估天赋与才能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慕尼黑 2010
- 《慕尼黑天赋研究》,Heller 主编 2010 (ISBN: 3643107285)。文集。
- 「慕尼黑纵向天赋研究的发现及其对识别、天才教育与咨询的影响」,Heller 2013:
「慕尼黑纵向天赋研究」(MLGS)最初于1985-1989年间实施,并在九十年代完成了两次追踪研究。该研究在第一阶段聚焦于三个目标,第二阶段则扩展至五个。从九十年代中期至2010年底,慕尼黑大学(LMU)天赋研究中心基于MLGS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开展了一系列后续研究。首先,本文将阐释作为MLGS及后续研究理论框架的「慕尼黑天赋模型」(MMG)及其扩展版「慕尼黑动态能力-成就模型」(MDAAM)。在介绍研究方法后,本文将详细呈现MLGS的部分重要发现。下一节的重点是这些发现在识别天才个体及为天才项目选拔人才方面的实际应用。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基于MMG和MDAAM并经过科学评估的干预策略与措施,它们旨在提升个体潜能,同时减少无效或功能失-调的动机变量及自我概念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在STEM领域和针对高风险群体)。最后,文章将对研究结论进行讨论。
[4] 本卷收录的另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是 Johnson 与 Bouchard 2014年的《与创造性天才相关的智力及人格特质遗传学:天才能成为宇宙龙王吗?》。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SMPY Bibliography · Gwern.net
作者:Gwern Bran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