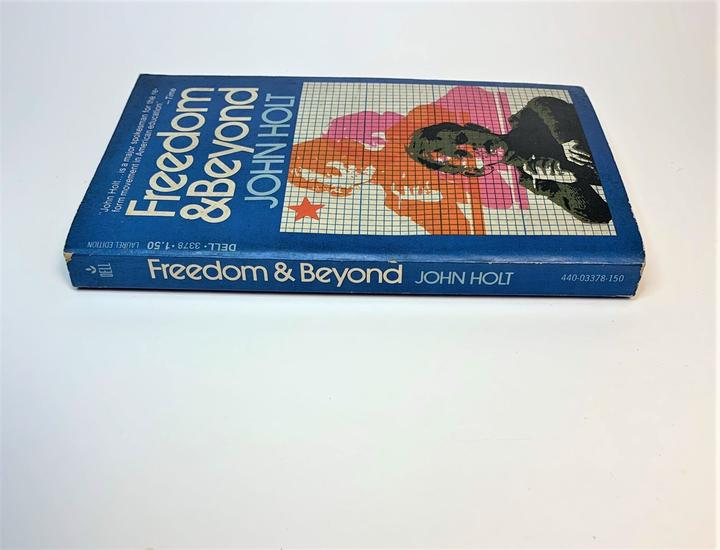两个孩子,姐姐八岁,弟弟五岁,正在房后的草地上玩耍。我在一旁看着,偶尔在他们要求时帮把手。他们的主要工具——或者说玩具——是一根长长的晾衣绳,一端系在一棵小树上。八岁的姐姐正和学校里的许多朋友一起学习跳绳,所以她想玩些与跳跃有关的游戏。五岁的弟弟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不管姐姐玩什么,他都想掺和进去。他们经常一起玩,部分原因是虽然他们也有其他朋友,但住得都不够近,没法想玩就玩;部分原因纯粹是因为姐弟俩感情好。就像孩子们常有的那样,他们此刻正处于一种想要争强好胜的情绪中。
这场游戏是八岁的姐姐组织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弟弟也常是带头人——她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而且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做。其中一个游戏是跳高。绳子的一端系在树上,离地大约两英尺。她指示我站的位置,把绳子的另一端交给我,让我把绳子升高或降低到特定的高度。我们从低处开始,她跳过去,让我把绳子升高一点,再跳一次,依此类推,直到高度达到她的极限。在另一个游戏中,我们把系在树上的绳子稍微往上挪一点,我甩动我这一端,她练习「跳进去」,这动作她还不太熟练。她希望能像班上其他女孩一样做得那么好。
弟弟也在场,他也想加入进来。这就造成了困难和紧张。困难在于他几乎完全不会跳高,更别提跳甩动起来的大绳了。姐姐的游戏里没有适合他做的事。在看姐姐跳了几次后,他开始吵嚷着要轮到他。这种紧张源于两种相互冲突的拉力、需求或欲望。一方面,姐姐想继续练习。另一方面,如果她把弟弟晾在一边,他会生气的。他要是生起气来可不得了,而且既然他们住在一起,这事儿总得解决,总得想办法安抚他、平息他的怒气、把他哄回来,让他重新变回好朋友。况且,跳绳游戏不会一直玩下去,玩别的游戏时她还需要他。再者,她也喜欢弟弟。所以,在不放弃自己的游戏和比试的前提下,她必须想办法让他也参与进来。
所有这些算计听起来非常费劲且刻意,但事实是,她在玩耍的过程中就在思考或凭直觉感知到了这些现实情况和需求。她在考虑如何安排弟弟时,游戏并没有中断。在跳高游戏中,这很容易处理。她跳几次,然后我们把绳子放低,几乎贴近地面,让他也跳几次。在另一个跳绳游戏中,她向弟弟——也向我——介绍了一个叫「Blue Bells」(蓝铃花)的游戏,这真是一个奇妙而巧妙的游戏,想必是孩子们为了学习跳大绳而发明的第一步。在「Blue Bells」中,绳子只是前后摇摆,孩子趁绳子荡向自己时跳过去。他必须学会让自己的助跑和跳跃配合绳子的摆动节奏。结果正如姐姐所料,这个难度刚好既能挑战他、让他兴奋,又足够简单,让他大部分时间都能跳过去。
于是游戏继续进行。两个孩子都很活跃,玩得很开心。但这其中仍有挫败感和紧张气氛。两个孩子都想要一场真正的比赛,但这并不是比赛,他们心里都清楚。弟弟几乎不会跳高,连「Blue Bells」也只能勉强应付,他自己也看得出,这离能跳大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姐姐想要一个水平相当的对手,以此来激励自己,增加游戏的刺激感。弟弟则想把游戏变成另一种形式,好让两人技能上的差距不那么巨大或明显,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笨手笨脚的人,而是一个像样的对手或伙伴。因此,他们必须对彼此做出微妙的调整。如果姐姐在自己擅长而弟弟不行的项目上花太多时间,弟弟就会感到沮丧、生气并退出。她绝不能过分炫耀自己的技能,让弟弟难堪。同时,弟弟也必须欣然接受一个事实:暂时这是姐姐想玩的游戏,而且没办法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掩盖姐姐比他强得多的事实。如果他对输赢太较真,姐姐就会不再带他玩,让他自己一边玩去,然后继续做她自己的事。
就这样,他们带着极大的微妙和技巧,在玩耍中相互调整以适应对方的需求和感受,对他人的言行做出即时的反应。这一切都伴随着活力和喧闹。确实,随意的或粗心的观察者可能会认为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争吵或打架。其实不然。他们只是在做大多数长辈已经忘记如何做或不敢做的事,那就是坦率地表露当下的真实感受。正因为他们如此公开地表露感受,才能如此迅速而熟练地进行相互调整。当他们对对方的举动不满意时,他们不会把不悦或怨恨藏在心里,任其发酵成无法收拾的怒火。他们会立刻通过言语或行动发出信号,告诉对方事情不对劲,必须做出改变。
我以这个故事开篇是有原因的。这本书是关于学习中的自由,同时也探讨当我们试图创造让学习者自由学习的情境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紧张关系。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情境是新奇的、陌生的、尴尬的、令人困惑的,甚至是具威胁性的。我们发现甚至很难学会如何去感知它们,如何看清和听懂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发现要置身其中、应对它们并充分利用它们,更是难上加难。这项任务本就困难,如果我们试图用不恰当、无法描述实际情况的词语来讨论这些情境,它很快就会变得不可能完成。我们要审视我们的语言。如果用词不当,我们将无法看清或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有一组词,扭曲并掩盖了真相和理解,那就是「结构化——非结构化」。几乎所有谈论或撰写关于开放、自由、非强制、学习者主导的学习情境的人,都把这些情境称为「非结构化」的,而将其对立面——传统的、专制的、强制的、教师主导的情境——称为「结构化」的。支持开放式学习的人和反对它的人一样,都在这样使用这些词。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世上不存在所谓的「非结构化」情境。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人类情境,无论多么随意和自然——这也是我讲孩子们玩耍故事的部分用意所在——都有其结构。
如果两个人偶然在街上相遇并交谈了半分钟,这次会面也是有结构的,甚至可能非常复杂。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彼此是什么关系?他们地位大致平等,还是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拥有某种权力?这次相遇对双方来说都同样受欢迎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如果是,原因相同吗?其中一方是否想让另一方做某事?他认为另一方想做吗?另一方愿意做吗?
我们可以提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将与那次街头会面的结构有关。而且,这次会面的结构还存在于许多其他结构之中。对于每个人来说,这只是其包含万千事物的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会面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特定类型城镇的特定街道上,处于某种文化背景中;在这种文化中,这些人根据其经济和社会阶级,被期望并也期望自己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
我们所有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各种结构之中。这些结构本身又存在于其他结构之中,而那些结构又被更大的结构所包围,就像中国套盒一样层层嵌套。这一点对儿童来说同样适用。他们生活在家庭的结构中;家庭之外是邻里社区,他们对社区有着特定的感受。这个孩子还生活在他的朋友圈和学校的结构中。如果他是生活在怀俄明州北部的牧场上,他的生活将会截然不同。
孩子们对这些结构并非无动于衷。他们感知它们,凭直觉体察它们,想要了解它们,学习如何适应它们,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我们不需要把结构强加给孩子的生活。它本来就在那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许多孩子——包括许多贫穷的城市孩子——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结构,有太多的情境让他们必须时刻担心什么是正确的事,担心自己是否想做、敢做,或者敢不敢拒绝去做。正如 Paul Goodman 所精辟指出的,他们真正需要的往往是一个逃离这一切的机会——更多的独处、时间和空间。
在我与许多其他人极力倡导的开放式(或自由)教室与传统教室之间,当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是通过给这些班级贴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标签就能解释清楚的。甚至指出开放式班级实际上比传统班级拥有更多而非更少的结构,也无法完全说明问题。让我们换个角度,谈谈两种不同类型的结构,看看它们有何区别。
我们可以说,传统教室的结构非常简单。打个比方,它里面只有两个元素,或者说两个活动部件。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学生。孩子们可能各不相同,但在这样一个班级里,他们的差异无关紧要。他们都要做同样的事情,而且被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去做。就像流水线上的工厂工人,或者军队里的士兵,他们是可以互换的——而且往往是随时可被牺牲弃用的。关于这种结构,我们能说的第二点是:它是僵化、刻板且静止的。从开学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它都一成不变。最后一天和第一天一样,老师在发布信息和指令,而孩子们在被动地接收、服从或拒绝服从。关于这种结构,我们能说的第三点是:它是武断且外在的。它不是从班级的生命和需求中生长出来的,与孩子们想要什么、老师能给予什么毫无关系。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从上方直接罩在他们头上。在这个结构中,老师和孩子们一样,都是囚徒和受害者。对于这个结构应该是什么样,老师并不比学生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在改变它这方面,老师能做的也比学生多不了多少。
相比之下,开放式班级的结构是复杂的。教室里有多少老师和孩子,它就有多少个元素。这些元素中没有哪两个是一样的,而正是这些差异造就了所有的不同,因为没有哪两个孩子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与班级及老师建立联系或利用他们。其次,这种结构是灵活且动态的。每个孩子与老师及班级的关系每天都在变化,甚至在一年之中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实际上,整个班级的性质都可能发生改变。最后,这种结构是有机的、内在的。它生长于孩子和老师们自身的需求与能力之中。他们创造了这种秩序,正如 James Herndon 在 The Way It Spozed to Be (原本该有的样子)或 George Dennison 在 The Lives of Children (孩子的生活)中所生动描述的那样——或者就像我开篇故事里的那两个孩子一样。当这种秩序由他们创造,并正因为是由他们创造时,它才行之有效。我并不是说它看起来整洁漂亮;它往往并不整洁。我的意思是,它能帮助人们把事情做成,帮助他们生活、工作和成长。它不会扼杀生命力,而是增强它。
一个班级的结构还可以是清晰的或模糊的,直截了当的或自相矛盾的。这与它是否开放没有太大关系,除非是非常严格的传统教室,它们通常既清晰又直截了当——你在那里做任何事都可能惹上麻烦。孩子想了解关于班级的是:规则容易发现吗?还是很难搞清楚?一旦发现了规则,它们靠得住吗?有些群体说:「这里的规则没问题,一切都是公开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另一些群体说:「我们没有规则,我们不信规则那一套。」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所有群体都有规则,而且所有的规则都比能写下来的要多。构成一个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拥有的规则比它意识到的要多。群体中的人们以相同的方式做很多事,甚至从未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一个局外人进来,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我曾经认识的一所学校过去常吹嘘其唯一的规则是「走廊内禁止滑旱冰」。简直是胡扯。学生们心里很清楚,有很多事情如果你做了都会惹上麻烦。
在任何教室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开放的,僵化的还是灵活的,孩子们都想知道如何相处,如何成为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如何分得一杯羹。最重要的是,套用那句人人都爱用的短语,他们想知道「界限在哪里」。如果做某事或说某话会让他们陷入大麻烦,他们想预先知道那是什么。就像宪法禁止「事后法」(ex post facto law)一样,孩子们也不喜欢这种做法——掌权者(老师)判定你做的事是犯罪,但在你做这事之前却不说这是犯罪。暴君总是故意让法律模糊不清。含泪的孩子:「但我做了什么?」复仇的成年人:「你很清楚你做了什么!」
班级的结构、规则和习俗在明确表述的意义上是否清晰,其实没那么重要。孩子们习惯于在复杂的人际情境中自行摸索规则。他们不喜欢的是自相矛盾的结构。在早期的进步学校,而且我怀疑在现在的相当一部分「另类学校」中,成年人对孩子们将要和应该如何表现有着强烈的期望。他们把自己关于「人类一般应有的正确行为」的理论投射到孩子身上。他们认为:「如果孩子们心理健康,他们就会表现得像我们认为大家应该表现的那样。」就这点而言,这可能对所有老师都适用,不管是不是进步派。区别在于,传统老师会直接告诉孩子们他希望他们如何表现。而进步派或所谓的自由派老师则说:「你们想怎么表现都行。」于是孩子不得不寻找线索——那些成年人忍不住流露出的线索——来判断自己做得对不对。这可能让人筋疲力尽。有时孩子受够了,就会像那个进步学校里著名的(可能是杜撰的)孩子那样说:「老师,我们今天非得做我们想做的事吗?」他的意思是:我们今天还得费劲猜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吗?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
当我刚开始走访许多学校和班级时,通过那些投向我的躲闪目光、悲切的声音和紧绷的动作,我看到在某些班级里,孩子们非常焦虑;而在另一些班级里,情况则好得多。这并不一定与班级的严格程度有关。从我的所见所闻中,一个我称之为「行为间隙」的概念开始在我脑海中形成。想象一个行为光谱,从「非常好」到「非常坏」。如果我们从「好」的一端开始向「坏」的一端移动,对于每位老师,我们都会在光谱上遇到一个点,称之为 A 点。这一点代表某种行为已经糟糕到让她烦恼,让她希望这行为停止,但还没糟糕到让她觉得可以、需要或应该采取行动去制止它。如果我们继续向「坏」的一端移动,过了一会儿我们会到达另一个点,B 点。这一点代表行为已经糟糕到让她觉得她能够、必须且将会采取某种行动去制止它。A点和B点之间的距离就是行为间隙。当这个间隙很宽时,全班都会感到不安;当它很窄时,他们可能会更自在——除非B点离行为光谱「好」的一端近得不可思议。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间隙的宽窄比它在光谱上的具体位置更重要。
这也为那句关于「儿童与界限」的老话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有用的解释。孩子们当然不喜欢那些对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感到厌烦的成年人。但他们同样不喜欢待在一个任由他们胡闹、任由自己被惹恼的成年人身边。这太神秘、太具威胁性了。当那个成年人终于忍无可忍爆发时,他会做什么?如果一个孩子正在做某件让老师烦恼的事,最好直接说:「嘿,停下来,这快把我逼疯了。」或者:「请不要那样做,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结构就是清晰的,孩子们能从老师那里获得信息,从而建立起对老师相当准确的印象,并学会如何与他共处。
上一章:
《自由与超越》第一章 前言下一章:待翻译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3-pro-preview,校对 Jarrett Ye
原文:FREEDOM AND BEYOND : JOHN HOLT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