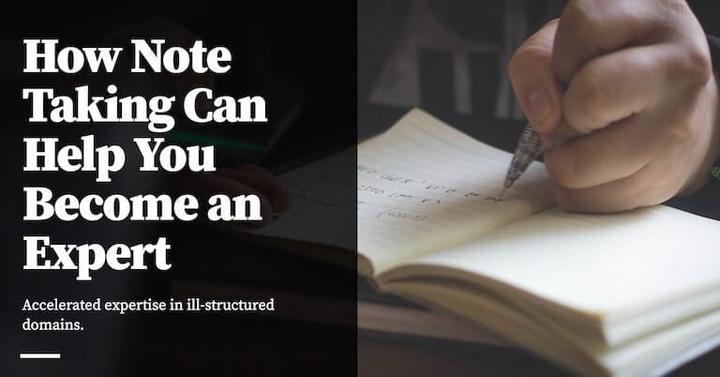目录:在结构不良的领域中学习:认知灵活性理论
在我们之前的会员专属文章中,我们探讨了认知灵活性理论(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ory, CFT),这是一种关于如何在结构不良领域中掌握适应性专业技能的理论。我解释了该理论的两大核心主张,但仍认为自己未能清晰阐述其核心理念,也没能讲清楚为何我认为它们颇具价值。经过过去两周的数次交流,我想我找到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来解释 CFT;你可以将本文视为上周文章的重述,并在文末附赠了可行的实践建议。
认知灵活性理论是一门有 30 年历史的学习理论,它最终引向了一个有些奇特的结论:它告诉我们,存在某种特定类型的笔记记录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历史中学习。在此过程中,它阐释了专业技能在结构不良领域中如何运作,撼动了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主导地位,并解释了如何正确地从经验中学习。
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从头说起。
如果你是 Commonplace 的长期读者,或许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CFT 正是支撑《加速专业技能养成》(Accelerated Expertise[1])一书的两大核心理论之一。该书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加速培训项目的最佳著作,最初是为美国国防部撰写并于 2016 年出版。(如果你还没读过我的总结[2],或许可以去看看;AE 是我去年读过的较为出色的书籍之一。书中涉及的另一个理论——认知转型理论(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Theory),在本博客的其他文章中有所涵盖)。
CFT 关注的是专业技能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它探问:「专家如何应对新情况?」这个专业技能研究的子领域,其恰当术语是「适应性专业技能」(adaptive expertise)。它最初由波多野谊余(Giyoo Hatano)和稻垣佳世子(Kayoko Inagaki)在 1988 年一篇题为《专业技能的两种路径》(Two Courses of Expertise)的里程碑级论文中确立。波多野和稻垣的观察大致如下:「当然,当然,我们现在已有大量关于『经典专业技能』的研究,比如人们下国际象棋,或者将同一个寿司卷重复制作数百次以臻完美。但那些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发明新开局,或者寿司师傅构思出全新菜单的情况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解释?我们又该如何训练学生做到这一点呢?」
稍加思索你就会发现,适应性专业技能关乎我们在职业生涯中将会面对的诸多情境。我们常常需要即兴发挥。由于我们所处的业务、行业或面对的客户各有其特定制约,我们常常需要应对并解决各种新情况。作为一名实践者,你在现实世界中面对的任何情境,都不会与商业书籍里阐述的框架完全吻合。正如波多野和稻垣所提出的问题:你该如何通过训练来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呢?
据我所知,CFT 是在回答这一问题上探索得极为深入的一个理论。关于 CFT 的一个主要注意事项是,它建立在加速高级医学教育的研究工作之上——想想看:(CFT理论面对的)是那些在医院体系中直面病患的初级医生,而非坐在讲堂里的一年级医学生。下文我将要描述的一切,都应牢记这一前提来进行解读。

认知灵活性理论的四大理念
认知灵活性理论(CFT)有两大主要主张,但在我们深入理论本身之前,必须先审视两大核心理念。我们将按顺序探讨。
理念一:CFT 关注结构不良领域
CFT 所着力的关键特征领域,是作者们所称的「结构不良领域」(ill-structured domain)。结构不良领域可以解释为:其中存在概念,但这些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实例化方式(instantiated)变化极大,而且极其混乱(messy as hell)。因此,实践者在结构不良领域中处理的大多数案例都将是新颖的。
例如,想想心脏病发作。心脏病发作是一个概念,是你在医学教科书里可以学到的东西。但心脏病发作的实际诊断却可能千差万别——它取决于患者的种族、年龄、性别、病史、潜在并发症等等;有些心脏病发作最初表现为消化不良,有些则可能持续数天。
关于如何进行心脏病发作的识别,这里有一个来自《力量的源泉》(Sources of Power)的故事:
一位护理人员描述了一次家庭聚会,那是她时隔数月第一次见到她的公公。
「我不喜欢你看上去的样子,」她说。
「呃,你自己看上去也没多好嘛,」他回答。
「不,我是说我真的不喜欢你看上去的样子,」她坚持道,「我们得去医院。」
他不情愿地同意第二天再去,但她坚持必须马上就走。检查结果显示一条主要动脉堵塞。第二天,他就接受了清除堵塞的手术。
请注意概念与概念实例化之间的区别:
我们许多人把心脏看作一个气球。一个人走得好好的,然后,「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戳破了气球,这个人就心脏病发作倒下了。这个比喻并不准确。心脏是一个泵,有着厚实的肌肉壁。它不会像气球那样爆裂,而是会像水泵那样发生堵塞。有时堵塞发生得很快,比如当血栓卡在某处时(这或许是气球比喻唯一沾点边的地方)。而当它在充血性心力衰竭期间缓慢堵塞时,则会显现出(其他的)迹象。身体中相对次要的区域获得的血液会减少。通过了解这些区域是哪些,并对其中几个区域表现出的模式保持警惕,你就能提前发现问题。皮肤得到的血液减少,会变成灰白色,这是最好的迹象之一。手腕和脚踝会出现肿胀。嘴唇可能呈绿色。我们对医生、护理人员和其他人的访谈揭示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指标。
不过,这只是一个医学领域的例子。让我们来谈谈商业,这是另一个结构不良领域。考虑一下「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这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种竞争优势。新手可能会读到「规模经济」然后想:「啊,这就是随着规模扩大,单位获客成本下降的时候。」他们甚至可能只固守于一个制造业的例子。
但请思考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一: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 60 年代末,时任德州仪器副总裁的张忠谋(Morris Chang)注意到,每次启动新的半导体制造流程时,初期都存在一个学习阶段,需要努力提升良率。当时的传统做法是从一开始就为芯片设定高价,因为新工艺的制造涉及巨额资本支出。张忠谋认为这种想法很愚蠢。他聘请了一批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顾问,让他们研究如何通过定价来扩大销量。最终,他们提出了一种叫做「学习曲线定价」(learning curve pricing)的策略——德州仪器初期以低价销售芯片,迅速抢占大量市场份额并将产量推至最大,这使得张忠谋和公司其他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快速沿着学习曲线爬升,从而提高良率(进而提升利润率)。随后,凭借其主导的市场份额,德州仪器会尽可能延长该芯片的生产周期,以收回初始的固定成本。张忠谋谈及那个时期时说:「我们会自动降价,然后每个季度持续自动降价,即使市场并没有要求这样做。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举措,尽管颇具争议。很多人认为我们很傻。既然没必要,为什么要降价呢?但我们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我们的市场份额确实在不断扩大。这项策略,再加上其他策略,使得德州仪器的集成电路业务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同时也是利润最高的 IC 业务。」(来源)
案例二:Netflix —— Netflix 从 2011 年开始大幅增加其债务负担,从 2014 年的不足 10 亿美元飙升至 2020 年的 160 亿美元债务——主要以垃圾债券的形式。这是一个规模巨大(且可以说风险极高)的赌注,但 Netflix 需要这笔现金来实现从流媒体提供商向内容生产商的转型。在《7 种力量》(7 Powers)一书中,Hamilton Helmer 如此描述 Netflix 的战略转型:「表面上看,Netflix 的举措似乎风险重重、野心过大。制作原创内容并因此锁定该内容的所有权利,成本更高昂。此外,Netflix 此前曾通过其 Red Envelope Entertainment 部门涉足原创内容领域,结果并不理想。因此,当时看来,这种前向整合似乎也可能被证明是『用力过猛』。但这些大胆、反直觉的举措最终被证明是改变游戏规则的。独家版权和原创内容使得内容——Netflix 成本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变成了一个固定成本项。任何潜在的流媒体竞争者现在都必须投入相同数额的资金,无论他们拥有多少订阅用户。举例来说,如果 Netflix 为《纸牌屋》(House of Cards)支付了 1 亿美元,而其流媒体业务拥有 3000 万用户,那么每个用户的成本就是 3 美元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只有 100 万订阅用户的竞争对手将不得不为每个订阅用户投入 100 美元。这是行业经济学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它终结了那种摧毁价值的同质化恶性竞争(commodity rat race)的阴影。」
请注意,这两个案例都是「规模经济」的实例,但每个案例的表达方式却截然不同。一个涉及制造业的学习曲线,这本身就不同于教科书中关于规模化降低单位成本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则利用了廉价债务、在资本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以及 2011 年前后流媒体行业的动态。换句话说,Netflix 之所以能将其规模转化为优势,是因为其在流媒体战争中的领先地位;若不谈论使其能够执行该策略的初始条件,就很难讨论其规模优势。
总结一下,「结构不良」的正式定义是「名义上属于同一类型的案例,其概念实例化方式高度可变」。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领域,可能会意识到其中某些部分是结构不良的,而另一些部分则不然——例如,在软件行业,计算机编程是结构良好的,但软件项目规划、软件设计、时间进度估算和安全事件缓解则相当结构不良。天哪,如果你思考任何一个职业或任何一个行业,你可能都会意识到其重要方面是结构不良的。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理念……
理念二:在结构不良领域中,案例与概念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CFT 断言,由于结构不良领域的这种特性,案例与概念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这第二个理念更为微妙,因此我们将花些时间来审视其含义。
我想我们许多人在学校都接触过一种特定的教学方式:老师先教一个概念,然后用作说明该概念的例子被视为可有可无、用完即弃的。我常用的例子是我们学习二次方程的方式——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两个例题,然后就期望我们记住解决此类方程的一般方法。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我们许多人内化了一种观念:概念是重要的,而例子则不然。
对于我们这些拥有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背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甚至更为普遍——我们被教导原则就是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例如,你会看到工程师在评价思维质量时,会轻蔑地说「你没有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思考」——其背后的假设自然是,在任何现实世界的分析中,简化推理(即,将问题分解到根本原因)和基于原则的逻辑是至高无上的。
顺便一提,这也是我个人被训练成的思考和论证方式——或许也是许多管理顾问类型的人被训练成的思考和论证方式:你提出一个主张,用一些推理来支撑它,然后给出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同时心里清楚,如果时间不够,这些例子是可以省略的。
但 CFT 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它指出,如果在一个结构不良领域中,概念的实例化方式变化极大,那么从第一性原理进行推理就会非常困难。
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我之前提到,CFT 源于对加速医学专业技能发展的研究。引向 CFT 的多个先导研究向我们表明:
- 如果只教授概念,经验老道的医生(Journeymen doctors)也无法识别具体病例。
- 他们无法从病人的症状表现反向推导出疾病的概念和机理。
- 新手倾向于固守从某个案例中得出的普遍教训,当遇到一个与他们头脑中原型案例截然不同的概念实例化时,就会感到难以接受。
- 事实上,结构不良领域中的专家是通过与过往案例进行比较来进行推理的,而非参考第一性原理。(来源:参见原始 CFT 论文中的引文)
如果你不相信最后一点,请回顾前面关于规模经济的两个例子。你能从每个例子中提取出什么样的第一性原理呢?是「经验曲线受益于高产量,因此你应该为最大化生产能力来定价」吗?但如果你所在行业的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这一点并据此定价了呢——就像张忠谋后来去创办台积电(TSMC)时所面临的情况那样?或者也许是「当你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且竞争对手尚未意识到你可以这样做时,发行垃圾债券将你的可变成本转化为固定成本」?这些所谓的「经验总结」听起来几乎是牵强附会——而且实际上很可能只是过度拟合了每个案例的特殊细节。
事实是,你无法轻易地将结构不良领域中的案例简化为可推广的原则。你常常必须将案例本身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在认知灵活性理论(CFT)的所有理念中,这是我最感挣扎的一点。
例如,我仍然相信第一性原理思维对于进行良好的「问题-解决方案」分析是必要的。在商业领域,你常常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需要解决的结构不良问题:你的客户流失率高于预期;你的销售效率低下;你似乎无法将员工留住超过一年。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进行一些粗略的模式匹配,然后直接跳到貌似可行的解决方案上。每当我这样做时,几乎总是追悔莫及。我发现,从「貌似可能的根本原因」的角度出发分解问题,然后根据某个解决方案可能产生多少信息来帮助判断哪组根本原因可能在起作用,以此对解决方案进行排序,这种做法更为有效。换句话说,我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进行思考的。因此,显而易见,我仍然相信第一性原理思维是好的,并且在实践者的工具箱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我必须承认,CFT 对案例优先性的强调,确实解决了我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问。
思考一下这个例子,疑问一:我阅读大量商业传记,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商业人士。我应该从 Facebook、英特尔(Intel)或台积电(TSMC)的故事中学到什么教训?换句话说:既然历史不会重演,而且在像商业这样结构不良的领域中,我将要面对的所有经历都将是新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对此,通常给出的答案是诸如「这样你就有更多模式可供比较」以及「为了建立背景知识」。但这仅仅引出了一系列后续问题:「为什么背景知识有用?」以及「当你面对新情况时,你又怎能指望使用模式匹配呢?」
CFT 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更连贯的答案,我们稍后会谈到。
这是第二个例子:我长期以来对查理·芒格的思维风格感到困惑。芒格是沃伦·巴菲特的商业伙伴,本身也是一位传奇投资者。他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卓越的选股者,你的头脑中必须拥有一个「心智模型的格栅」(latticework of mental models)。如果你是 Commonplace 的长期读者,大概对我批评那股似乎已席卷自助领域的心智模型热潮不会陌生。许多作者将芒格的方法推向了极端: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脱离具体情境的心智模型,却从未追问:芒格在实践中究竟是如何运用这些模型的?
因此,谜题就在于此:在我最初研究整个心智模型现象以来的这些年里,我读了很多芒格本人写的以及关于他的东西——而据我所知……芒格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进行类比推理。
我之前在总结《范围》(Range)一书时写到过这个例子:
「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在法律研究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并且随着律师们向我们寻求独特的见解和更易用的用户界面,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工具和内容,直到我们成为现有巨头的完全替代品。我们的技术可以高效扩展,因此我们也能提供更低的价格。」
查理看出了另一种模式。「这让我想起了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的『可乐大战』。直到大萧条之前,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定价相同,可口可乐主导着市场。但后来百事可乐将其每盎司价格降低了一半,销量随之猛增,利润也翻了一番。当存在优质替代品时,价格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武器。」
最终,查理向我们询问了更多关于融资计划的细节。我们告诉了他我们正在筹备的融资轮次以及一些其他参与的投资者。
「我敢打赌,」他说,「如果我投资了,我可以为你们当一回『犹大山羊』(Judas goat)。」
他注意到了我们困惑的表情。「你们不熟悉『犹大山羊』?」
我们摇了摇头。
「犹大山羊就是那只被从一个畜栏领到另一个畜栏、或是领进屠宰场的山羊,所有其他的牲口都会跟着它走。我敢打赌,如果我投资了,你们也会有很多其他投资者跟着签约。」(来源)
我一直觉得这很令人困惑。第一性原理思维难道不是「最佳思维方式」吗?那么为何这位极其聪明、极其智慧的人如此热衷于进行类比推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我们引向该理论的最后两个理念……
理念三和四:CFT 的两大主张
认知灵活性理论(CFT)提出了两大核心主张。专家如何在结构不良领域中应对新情况?换句话说,适应性专业技能的核心是什么?CFT 告诉我们,专家会做两件事:
- 他们通过组合过往案例的片段,来即时地构建一个临时的图式。
- 他们拥有作者所称的「适应性世界观」:这意味着,他们不认为对于在领域内观察到的某个特定事件,存在单一的根本原因、或单一的框架、或单一的模型可以解释一切。
这第二点有些微妙,因此我们需要稍微展开说明。
当你我(即非医生)想到心脏病发作时,我们脑海中可能会浮现一个心脏病发作的原型。也就是说,我们想象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理想」的心脏病发作场景——比如一个人倒地并捂住他或她的胸口。专家医生则不然。他们不会将像心脏病发作这样的概念简化为仅仅一个原型。相反,他们在头脑中拥有的是一系列原型,他们可以从中提取片段进行组装。
拥有适应性世界观意味着,每当你在一个结构不良领域中学习一个新概念时,你知道不能过度简化——也就是说,不能将其表述为单一的原则或概念。你不会试图去简化。相反,你知道要去搜寻新的、不同的案例,以便在头脑中积累一组原型,并让这组原型来塑造你对该概念的理解。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新的案例,你会更新这个概念,因为只有当你了解它在现实中是如何实例化的,这个概念才是有用的。
(请注意,该理论主张的是专家是的思考模式——当你询问他们时,他们很可能只会阐述一个简单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该概念在他们头脑中实际表征的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区别,所以我将让 CFT 的作者们来描述适应性世界观:
(结构不良领域中的专家)……关注案例丰富多样的细节,同时不那么强调概念的首要性(在结构不良领域中,概念对案例起着必要的辅助作用);使用多重而非单一的概念关系(如图式、原型、类比、视角等);将案例视为具有涌现属性的整体,使其大于各部分之和;增强对差异的敏感度,减少寻求相似性的偏见;认识到不可预测性、不规则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新情境下重新审视早期案例,以揭示先前情境中隐藏的侧面——非线性的重访并非重复;拥抱知识表征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非僵化;强调情境依赖性而非情境独立性;避免理解上的僵化,保持开放心态,认识到知识在新组合、新目的、新情境下有时具有无限的应用范围;依赖于根据情境适应性地组装先前的知识和经验,而非从长时记忆中检索完整的知识结构和程序……(摘自《牛津专业技能手册》第 962 页)
应用认知灵活性理论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 CFT 的四大核心理念,现在可以转向实践性问题:「我们该如何运用它?」答案是,我们将该理论的两大主张反转过来,便可得到教学上的建议:
- 你需要让学生接触关于每个概念的、尽可能多的案例,这样他们就能拥有一个丰富的片段素材库以供组装。
- 你需要向学生灌输适应性世界观。
研究人员建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研究案例的一个困难在于,人类并不擅长记住每个案例中所有「丰富多样的细节」——而且每个案例往往都交织着大量的概念。因此,研究人员推荐使用超文本系统——也就是一个你可以链接到其他笔记,或者链接到标签,再通过标签链接到其他笔记的系统。你让学生存储每一个案例,并要求他们高亮其中的概念。概念之间建立反向链接,指向其他相关案例。
这种方法有许多变体。许多基于 CFT 的学习系统会预先加载案例,并由专家医生或领域实践者进行了标记。学生们会接触到一个初始案例,该案例包含了特别丰富的高亮概念和特征(研究人员称这类案例为「十字路口案例」(crossroad cases),关于这一点稍后详述)。然后,系统会鼓励他们通过在案例、概念以及其他案例之间跳转来进行探索式学习。
系统的超文本特性解释了学生如何能够从许多不同的案例中组合片段。但你又该如何掌握「适应性世界观」呢?在《牛津专业技能手册》的相关章节中,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了四种方法:
- 在让学生探索系统之前,先给他们一个关于 CFT 思维模式的概述——基本上,就像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一样。(Jonassen, Ambruso, and Olesen, 1992)
- 让系统显示警句/口号(mantra)。例如,CFT 的教学常常调用诸如「没那么简单」或「视情况而定」之类的警句,随后呈现一个与前例截然不同的后续案例。
- 在学习系统中设计一个用于世界观转变的四阶段模型。这四个阶段如下——第一:通过创设一个情境来凸显学习者持有的简化世界观(比如前文提到的心脏病诊断例子,目的是让学生在某项任务中受挫)。第二:展示这种世界观为何是适应不良的(比如向他们说明将心脏比作气球的比喻是有缺陷的)。第三:介绍适应性世界观及其特性。第四:演示后者的运作方式,然后提供相应的练习活动以供掌握。(Spiro et al, 2007)
- 最后,探索 CFT 系统本身就能灌输适应性世界观。当学生探索超媒体系统时,他们会意识到同一个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实例化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变异性。
如何为自己构建一个 CFT 超文本系统?
《牛津专业技能手册》中关于 CFT 的总结有一节写得很好,介绍了如何为自己构建一个 CFT 学习系统。我将给你一个改编版本,我正在用它来试验标记商业案例,这个版本不要求你会编程。但请记住,我对此还是新手;给我几个月时间,我再写一些实践笔记。
第一步:选择一款具备反向链接功能的笔记应用。 反向链接(Backlinking)是一种功能,你可以选中一个短语,比如「规模经济」或「心脏病发作」,然后将该短语变成一个链接——看起来像 [[规模经济]] 或 [[心脏病发作]] 这样的形式。点击这个反向链接的短语,会跳转到一个界面,显示所有其他与「规模经济」或「心脏病发作」链接起来的笔记,这意味着你可以实现上文描述的「案例」 -> 「概念」 -> 「案例」的阅读模式。注意,你使用哪款笔记应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CFT 学习系统所倡导的特定认知方式。流行的应用包括 Obsidian、Logseq、Roam 和 Craft——随便选一个开始用就行。
第二步:开始将案例复制到你的笔记应用中,来源可以是文章、PDF、书籍或博客文章。用你观察到的概念或案例特征来标记特定的段落。 在标记的同时,将段落分割成更小的片段(segments),这样它们就有望在你的反向链接界面中显示出来。
分段的目的是让你在复习时,可以只理解/领会(grok)完整案例的一部分。当你在笔记中进行概念搜索时,你不应该需要重读整个案例——因此,片段很重要。
这个高亮和分段的部分有点棘手,因为正规的 CFT 学习系统会要求专家实践者为学生标记案例。可以想见,作为新手学习者,你会错过专家能够捕捉到的某些概念实例化或线索。但我认为这没关系——当你在为自己创建 CFT 系统时,这已经是你能做到的最好了。
不用太担心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分割案例——研究人员强调,将案例转化为片段并没有唯一的「正确方式」。(事实上,他们说「即使在方便的接缝处分割也大致同样有效」——这真的取决于你!)但不应该做的是,试图将案例组织成清晰定义的、同质化的阶段(homogenous stages)——当领域中存在时间要素时,比如病人的病史中症状随时间呈现,人们往往会这样做。这是因为,在结构不良领域中,即使大多数案例遵循相同的基础进展或结构,具体案例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
如何寻找要添加的案例? 研究人员建议从「十字路口案例」(crossroad cases)开始,即那些「富含对该领域至关重要的概念特征」并且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被视为该领域象征」(emblematic)的案例。研究人员建议初始阶段收集 10-20 个此类案例——事实上,所有的 CFT 学习系统都预装了 10-20 个十字路口案例的集合。
这反过来意味着,你必须寻找与你当前拥有的案例尽可能不同的初始案例。并且这意味着你应该持续寻找这类丰富的案例,直到达到收益递减的程度,那时你的核心十字路口案例集合可以说能够代表该问题领域了。因此,例如,如果你正在为心脏病发作创建一个学习系统,你会希望拥有 10-20 个能够代表现实世界诊断实践中最重要变异情况的案例。
第三步: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系统里要放什么。但你该如何使用这个系统来学习呢?
据我所知,基于 CFT 的学习系统通过两种模式运作,两者都是「组合式概念把玩」(combinatorial idea play)的表现形式:
- 你让学生访问 CFT 学习系统,然后给他们一系列任务去完成(我想象这就像给医生一系列难度递增的病例——「男性,63 岁,在楼梯底部被发现,多处挫伤……」,并通过诊断性问题进行评估)。CFT 学习系统是他们的参考资料库;他们的任务是在整个案例库中进行概念搜索,直到找到相关的片段,并给出他们最佳的猜测答案。
- 你让学生进行多次案例对比(multiple case contrasts),以便更快速地建立复杂的理解。如何鼓励这样做:你给他们一系列问题,比如「案例 A 与案例 B 有何相似之处,但与案例 C 又有何不同」以及「找出表面相似案例间令人惊讶的差异,并找出表面不同案例间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等等——从而反映专家理解的精妙之处。这种方法的一个变体是,观察一个过往案例的最重要方面如何在其他新案例的背景下发生变化(CFT 的一个口号是「重访并非重复」)。
这两种方法都迫使学生练习「片段的图式组装」。它们还有另一个作用:让学生过度学习(overlearn)那些十字路口案例!
现在我们来谈谈十字路口案例,为何它们重要,以及为何如此命名。当学生与 CFT 学习系统互动时,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那 10-20 个最丰富的案例。换句话说,当他们在案例间跳转时,很可能会在系统遍历过程中反复穿梭(criss-cross)于同样那几个最丰富的案例(因此得名「十字路口」案例!)。回想一下,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它们是该领域的「象征」(emblematic)。这会产生三个效果:
- 十字路口案例将迅速成为被分析最多的案例——这意味着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尽可能多角度地剖析(unpack)一个十字路口案例,从而实现对该案例的深度学习,并内化「案例是复杂的」以及「一个案例并非只关乎一件事,而是可以有多个可能的『标题』」——也就是说,结构不良领域中的案例关乎许多事情。
- 其次,随着十字路口案例在新的情境中被反复使用,它们很快会被「过度学习」。这意味着学生会对十字路口案例变得极其熟悉,以至于仅仅读到其中一小段独特的片段(研究人员称之为「缩影」(epitomés))就能唤起对整个案例的回忆,在认知上将整个案例历史「带入当下情境」。研究人员称这个阶段为「缩影模式」(epitomé mode)。一旦达到缩影模式,案例的组合和对比就可以以思维的速度进行。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学生在记忆中存储了一套可供调用和组装的案例——就像更有经验的实践者那样!
- 最后,十字路口案例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促进了许多概念实例化之间的联系建立。这主要通过我们上面提到的「案例对比」方法实现——每个十字路口案例被视为一个枢纽(hub),学生被要求在尽可能多的概念维度上找到尽可能多的相关联案例(辐条 spokes)。然后选择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案例作为枢纽,学生重复这个过程。
我猜你会说:这些道理听起来很受用。但当你在为自己构建案例库时,可以进行哪些活动呢?这是个好问题,我目前也不完全确定——给我几个月时间亲自实践检验一下。
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CFT 系统
在结束之前,最后再提一点。我认为在研读 CFT 相关资料时,发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是这篇题为《关于在结构不良领域中使用视频的后古腾堡认识论的反思》(Reflections on a Post-Gutenberg Epistemology for Video Use in Ill-Structured Domains)的论文中所描述的那个。
该论文描述了一个采用 CFT 式教学法的视频系统。作者们如此描述这个系统:
「因此,举例来说,在一个基于 CFT 的、用于教授阅读理解策略的视频系统中(Palincsar, Spiro, Kucan, Magnusson, Collins, Hapgood, Ramchandran, & DeFrance, 即将发表),『支架』(scaffolding)这个主题概念的教学,首先是让学习者观看大量教学中运用『支架』的实例。然后,他们逐渐认识到『支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无法为其预设一个能够充分指导实践应用的定义。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影响该概念应用方式的各种丰富多样的情境特征的展示。」
「我们的一个界面功能,即『Weave』模式(它允许四个视频片段在同时出现的象限中进行比较——这个功能可以在之前提供 URL 的 EASE History 系统中看到),能够支持一种有助于人们理解此类概念家族的结构不良特性的练习。我们要求使用者利用 Weave 界面设置四个属于同一概念类别的视频片段,然后让他们识别出其中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即那些表面看似不同,但仔细审视后可被视为同一概念实例的片段)和令人惊讶的差异之处(即那些表面看似相似,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在某些有趣方面有所不同的片段特征)。学习者很快就会打消关于意义和概念使用的简化观念;同时也能对特定的概念产生更丰富的意义感。」
研究人员谈论的是阅读理解策略,但我的思绪立刻转向了比赛录像。我常常发现在尝试学习一项柔道新技术时,回顾视频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不得不用笔记应用手动追踪技术的各种变化,并附上指向特定 YouTube 视频或时间戳的链接。而 Spiro 等人在其研究中描述的几乎所有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柔道——各种投技(throws)可能看起来相似,但对于某些投技而言,其准备动作(setups)、握法(grips)、进入时机(entries)和具体执行(execution)都可能变化极大。举个例子,柔道的投技「内股」(Uchimata)至少有六种不同的进入方式和五种不同的握法,用于不同的格斗情境,尽管在概念层面上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投技。
现在,将这种界面和这种学习理论应用到,比如说,Dota、足球、甚至是计算机编程直播上。设想一下,我们可以用概念元数据来标记视频片段,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视频、概念、选手、风格等不同维度之间自由跳转。再设想一下,我们可以在一个四象限界面中慢速回放并比较不同的视频片段。通过这种方法,可能会创造出怎样全新的学习体验呢?
结语
我介绍了一个有 30 年历史的理论,它解释了如何在结构不良领域中更好地学习。我们最终抵达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一个旨在加速专业技能养成的笔记记录学习系统。在此过程中,我们审视了专家在面对新情况时的表现,我们对第一性原理思维提出了质疑,并且我们考察了结构不良领域中专业技能的若干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精通之路颇为艰难。
在这个阶段,我必须坦承一件事。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将「更好的笔记记录」视为一种提升思考能力的方法持抵触态度,更不用说将其作为加速专业技能获取的途径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系统,它同时满足以下几点:a) 有着实际应用的记录;b) 对学习的底层认知科学有着连贯一致的解释;并且 c) 能够解释它如何在混乱的领域中取得成果。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认知灵活性理论(CFT),还有多少东西有待我们去发现?我们可以从过去 30 年的系统实践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又存在哪些系统性的失败和盲点?
我不知道,但我打算去一探究竟。
来源
- The single best resource for CFT is probably the summary chapter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xpertise. This isn’t available online, though I’ve included a scanned copy for memb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previous (members-only) post.
- 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ory: Advanced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Ill-Structured Domains by Spiro, Coulson and Feltovich is the original 1988 pap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 Reflections on a Post-Gutenberg Epistemology for Video Use in Ill-Structured Domains is the most impressive system implementation I’ve found so far.
- Jonassen, D. H., Ambruso, D. R., & Olesen, J. (1992). Designing a hypertext on transfusion medicine using 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ory.
上一篇:
从他人经验中学习的最佳方式 - 知乎下一篇:
原则本身并无用处 - 知乎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exp,校对 Jarrett Ye、Horla lu
原文:How Note Taking Can Help You Become an Expert - Commoncog
作者:Cedric Chin
最初发表于 2022 年 2 月 8 日,最后更新于 2022 年 7 月 6 日。
参考
1. 加速专业技能养成 ./1893600889685669818.html2. 加速专业技能养成 ./18936008896856698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