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天才是如何培养的
原文:How geniuses used to be raised - by Erik Hoel
贵族式辅导 III:日常实践揭秘
2022 年 11 月 2 日
近来,大公司似乎特别热衷于用机器取代人类天才,但我认为,现在就对人类失去信心还为时过早。为此,我写了《我们为什么不再出产爱因斯坦》一文,探讨历史上那些天才人物往往是工匠式教育精心塑造的结果——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天才,他们身边围绕着成群的家庭教师和私人导师(而这些导师本身,往往就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或各自领域的顶尖专家)。
这种不平等的贵族式教育显然无法匹配现代教育体系的大规模培养需求,而放弃贵族式辅导很可能导致了天才和通才的减少。尽管今天的孩子们接触成年知识分子的机会更加平等,但这种接触往往变得零散而稀薄,远不如旧时特权阶层孩子所享受的那种「集中熏陶」(我必须强调,这极其不公平)。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他 1961 年的讲座集《物理学之美》(Six Easy Pieces)中,总结了一对一辅导的益处及其规模化实施的困境:
但是,我认为,要解决教育问题,必须认识到:最好的教学,只可能发生在师生之间直接建立的个体连接中。唯有学生与良师一对一探讨观点,自由交流,探讨想法,思考问题,教育才能达到理想状态。仅仅坐在教室听讲,甚至只是完成布置的作业,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学生太多了,我们不得不在这种理想状态之外,寻找一个替代方案。
那么,如果能不计成本投入教育,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日常教育方法能稳定地「出产」天才?
首先说明,我研究贵族式辅导,是要梳理出一套关于其结构和理念的指南,尽管比较抽象,但或许有助于复兴这种教育方式。当然,最好更加公平,比如借助新技术,让中产家庭也负担得起。一对一辅导可能永远无法普及,说实话,精英教育本就不是人人负担得起的。教育成本一路飙升,顶级私立高中一年学费高达 7 万美元,可统计数据却很难证明把孩子送进去就能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学生贷款债务逼近两万亿美元,而大学(我在里面待了快二十年,深有体会)却似乎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营业化,更像是给年轻人提供的服务场所,而非培养天才的殿堂。教育陷入如此困境,我们有理由憧憬一个不同的教育图景。

作为培养众多(即便不是大多数)杰出人才的摇篮,贵族阶层自启蒙运动早期就盛行一对一辅导。长达几个世纪,辅导都是教育的主流形式。它在贵族阶层发展成熟,而后被社会各阶层效仿实践:比如富一代(new money)模仿贵族聘请教师,或者少数情况下,中产或贫困家庭的父母亲自上阵。
就连孤儿,有时也能得到贵族式辅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通常被描绘成(比如音乐剧《汉密尔顿》里那样)完全白手起家、简直是天纵奇才、聪明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汉密尔顿给母亲当过记账员,母亲去世后,这段经历帮他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找到份文员工作,替老板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 Cruger)处理物流事务,而克鲁格对这个年轻人也格外用心培养。此外,汉密尔顿还有另一位尽心尽力的导师,一位才华横溢的牧师:
诺克斯(Knox)在汉密尔顿的母亲雷切尔去世不久后便开始照顾他。这位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因坚信自由意志而反对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教义,与主流信仰格格不入。对汉密尔顿这种似乎注定一生默默无闻的人来说,诺克斯的哲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位牧师的鼓励和影响,无疑点燃了汉密尔顿内心的雄心壮志。诺克斯不仅布道词写得出色,偶尔也行医,他将这名年轻孤儿护在翼下,亲自辅导他学习人文和科学。工作之余,汉密尔顿总爱泡在诺克斯的藏书室里,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类经典著作、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持续拓展着知识边界。
除传记所载的诸多案例外,还有证据显示,剑桥和牛津大学曾有几十年根本不开讲座,教育体系完全围绕一对一辅导展开,这恰好和牛顿等诸多伟人就读的时期重合。当时的导师们不仅主导大学的管理,甚至直接向学生收取费用。古典教育著名的收官环节「欧洲壮游」(Grand Tour),也是由这些富家子弟的导师带队。纵观历史,从笛卡尔到巴斯德,众多学者都通过担任贵族私教谋生。甚至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富家子弟就聘请私人教师在家授课,只有平民子女才会进入类似我们今天这种形态的学校。
那么,从这些历史片段中,我们能提炼出哪些切实可行的见解?
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例,他堪称历史上「精心培养的天才」中最典型的案例之一。他在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领域都成就斐然,是那个时代的巨擘。密尔写了一部详尽的自传,向后人披露了他的教育历程(下文所有引用的密尔的话均源于此)。这可能是那个时代关于贵族式辅导最翔实的记录了。而辅导他的,正是他父亲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密尔写道:
记录下这样一种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教育或许是有意义的。且不论它还有何建树,这种教育起码证明:在那些普遍的所谓「教学」模式中几乎被荒废的幼年阶段,能教授并被有效接受的东西,远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多得多。
密尔这样描述他父亲詹姆斯·密尔的付出:
在那整个时期,父亲几乎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教导子女:尤其对我,他更是倾注了超乎寻常的精力、心血和耐心,极力按照他的教育理念,给予我最高水平的心智培养。
詹姆斯·密尔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教育方法(在另一位天才人物杰里米·边沁的建议下),采用的正是那种贵族式的辅导模式,这在当今时代已无法复制。例如:
父亲从不允许我将学到的任何东西退化成死记硬背。他坚持让理解伴随教育的每一步,甚至争取超前。凡是能通过自己动脑解决的问题,他绝不会直接给出答案,直到我自己用尽方法独立思考找出答案。凭心而论,我在这方面做得相当笨拙;回忆起来几乎全是失败的经历,少有成功的时候。
也就是说,贵族式辅导者会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关注过程和基本原理,避免无效记忆(这和现在的学校教育背道而驰)。当然,有些情况下大量记忆在所难免,比如密尔三岁时他父亲教他希腊语的情景:
我对此最早的记忆,是背诵父亲称之为「词根」(vocables)的东西,就是父亲写在卡片上的一系列常见希腊词列表,配上英文意思。
密尔后来写道,他阅读了:
在父亲指导下,我读了很多希腊散文作家的作品,我记得的有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全部著作,还有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Cryopaedia)和《苏格拉底的回忆录》(Memorials of Socrates)……
但这并不意味着密尔什么都学——他父亲的教学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先是希腊语,然后是算术和历史,初期很少碰其他科目。从语言入手是贵族式辅导的常见路子,通常由家庭女教师负责,有时也像密尔这样,由父母或男导师亲自教导。当时普遍认为,数学需要心智更成熟才能领悟,而语言、历史和文学则天然适合早期学习(注意,这和现代学校试图让所有学科齐头并进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密尔从小就被允许自主研读、探索课题。以算术为例:
这也是父亲教我的:它是晚上的任务,我清楚记得那有多么枯燥。但这些课程只是我日常学习的一小部分。更多来自我自发阅读的书籍,以及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尤其是在我们散步的时候……读书时我会在纸片上记笔记,然后在晨间散步时,就依据这些笔记向他复述内容……
想想这和现代的一对一辅导有多大差别:如今的辅导多半是找个学长学姐在咖啡馆刷 SAT 题。而贵族式的方法则更从容,也更灵活,有时甚至在散步时效果最好。
密尔自己也常常担任「贵族式导师」的角色,去辅导弟弟妹妹。
我八岁开始和一个妹妹一起学拉丁语。我边学边教她,她学完再向父亲复述……不过,我从这种锻炼中获益良多:那些需要教给别人的知识,我学得更扎实,记得也更牢固;或许,在那个年纪练习向别人解释难点,本身就是一种有益的锻炼。
这同样是宝贵经验:让孩子亲自当老师颇有益处。在以讲授为主的标准化教育体系里,很难想象让这么小的孩子去教别人——如果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辅导,他们怎么知道如何辅导别人?可见,早期的儿童辅导能打开常规教学模式难以实现的可能性。
学完算术后,密尔又在父亲指导下学了欧氏几何几何与代数。到十一二岁,密尔已经开始开始撰写历史和研究文章,算得上是短篇论文了。父亲对此表示鼓励但从不审阅,以免过于严厉的评价打击他的热情。我再次认为这是宝贵经验:对一个用心良苦且有才华的导师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变成一个权威的批评者,这会扼杀创造的乐趣,让智力探索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心生畏惧。所有早期的智力成果,都注定如同孩童堆砌的沙堡,短暂而脆弱。
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在大学招生时,「全面发展」最为吃香。但在天才的成长故事里,我们常看到导师鼓励他们尽早钻研特定领域。密尔还不到十几岁,就开始帮父亲做学术研究(布莱士·帕斯卡开始帮父亲时也差不多这么大),这表明贵族式辅导在某个阶段应该升级为更高级的模式,类似学徒制或合作制——很像现在教授和研究生的关系,只是发生的年龄要早得多。
就密尔而言,这种合作大致是这样:他和父亲每日散步时围绕同一主题展开深度探讨,父亲会从不同角度深入阐述,密尔则保持着一贯的笔记习惯。这种聚焦式讨论持续多日。之后,密尔会整理出一份结构清楚的初稿,以帮助父亲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最终父子二人会共同审阅这些初稿,进行深入推敲:
直到它清晰、准确、内容也像样了。我就这样把整个学科过了一遍;我每天提交的 compte rendu [报告]整理成的书面大纲,后来就成了他写《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的参考笔记……这种教学方式堪称培养思想家的绝佳方法,但需要由像我父亲这般严谨有力的思想家来实施……我不相信还有哪种科学教学能比这更透彻,更能锻炼思维能力……他极力(甚至有些过度地)激发我的能力,让我凡事自己去探索,他的讲解总是在我探索之后,而不是之前……
想想看,詹姆斯·密尔仅仅通过散步,就如此自然地推动了儿子的进步。起初,儿子只需记录父亲即兴讨论的内容,隔日共同温习笔记。几年过去,这逐渐演变成了学徒模式,父亲重拾旧题,而儿子则帮他写下他的下一部著作。
这和亚里士多德教导学生(包括亚历山大大帝,据说他行军时总带着亚里士多德赠送并批注过的《荷马史诗》)的方法如出一辙,或许并非巧合。实际上,许多我们现在认为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作品,比如他的《修辞学》,最初可能只是学生为辅助教学整理的笔记,而非为了出版。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划时代的宏篇巨著,在当时也许只是辅导过程中的练习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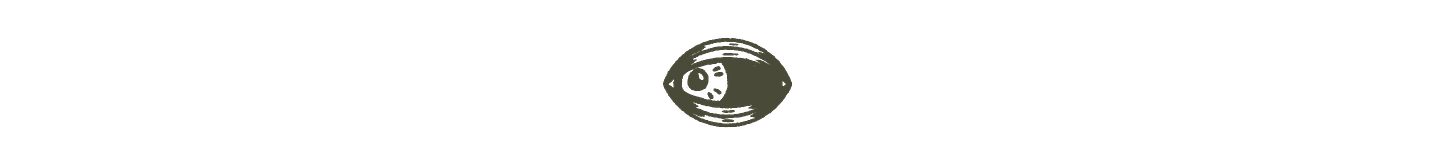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有详实自传记录的贵族式辅导案例——伯特兰·罗素的教育。但他的经历大相径庭。不同于密尔有父亲专职辅导,罗素的导师换个不停,可能多达几十位。不过,他的家庭依然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在《罗素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中有细致描述。
我的罗洛叔叔(一位气象学家)在我早期成长中很重要,他常常跟我聊科学,他在这方面懂很多……他的谈话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
他的阿加莎姑姑也是。罗素这样回忆和姑姑的相处:
我六七岁时,她又开始教我,教的是英国宪法史。这让我兴趣盎然,她教的很多东西,我至今还记得。
放眼今天,你能想象哪个姑姑会这样教孩子历史,而且还是每天坚持、一丝不苟地教吗?这种情况在罗素家屡见不鲜:11 岁时,罗素的哥哥就开始教他欧氏几何。
事实上,和密尔相似,罗素那些极为聪慧的家人进行的早期辅导,常常让他的笔记本里充斥着成年人的长篇大论和各种解释,而年幼的罗素更像是个速记员。其他时候,他们只是单纯地一起读书,比如罗素回忆给祖母朗读的场景:
在我能流利阅读后,我常读书给她听,就这样,我广泛接触了标准的英国文学。我和她一起读了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顿、库珀的《任务》、汤姆森的《懒散之堡》、简·奥斯汀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书。
正是罗素的祖母精心规划了他所受的教育,而她这么做是为了避免重蹈长孙的覆辙——那位长孙因为受不了她那种咄咄逼人的宗教热情,把她的信看都不看就烧了。根据《伯特兰·罗素传》,她这么做的原因是:
至少要让伯蒂(Bertie)保持纯洁、虔诚和友爱;必须把他培养成能接替祖父首相之位、继续推进神圣改革事业的人才行。
(注意这和詹姆斯·密尔的想法多么相似,对他来说,儿子就是承载并延续功利主义思想的希望)。也正是罗素的祖母让导师们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罗素自己猜测,这或许是为了避免削弱她对他的掌控力。同时,她又怕他太累,所以尽量压缩罗素的正式课业时间。
罗素身边还有几位住在彭布罗克庄园(Pembroke Lodge)的家庭女教师,比如德国保姆威廉明娜(Wilhelmina),她们在奖惩方面通常有很大的自主权。
……我变得非常依赖她。她教我写德文信…… 她偶尔也会打我,我记得被打时会哭,但这从未让我觉得她因此就不再是朋友。她一直陪我到六岁。
(关于家庭女教师对天才成长的影响,真够写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的了,因为太多人在默默无闻中扮演了早期启蒙者的角色。)
男导师不仅和家人同住,有时甚至就在彭布罗克庄园的地界上搞科学研究。罗素在描述一位这样的导师时写道:
他信奉达尔文主义,当时正在研究小鸡的本能。为了方便他研究,那些小鸡被允许在屋里每个房间「横行霸道」……
学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罗素的进步似乎常取决于导师的水平。最差劲的导师只会照搬上课的那种死记硬背和照本宣科。
我发现代数入门难多了,也许是教得不好。我被要求死记硬背:「两数和的平方等于两数的平方和加上两数乘积的两倍。」我压根不懂这是啥意思,记不住时,导师就把书往我头上一扔,这对启发我的智力没任何帮助。不过,熬过代数入门的坎儿后,后面就都顺利了。我以前还挺喜欢用自己懂的东西给新来的导师一个下马威。
到了 18 岁,罗素和密尔一样,从被辅导者变成了学徒,给传奇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当助手并合作,最终共同完成了名垂青史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然而,他们的关系最终和许多紧密的师徒关系一样,以决裂告终。因为《数学原理》虽然才华横溢,却终究不过是试图填补逻辑与数学核心缺陷的悲壮尝试。但他们确实密切合作了整整九年,关系近到有时会在对方家一住就是几星期。持续的讨论与辩论对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精神刺激,罗素想必时刻都感受着电流穿身般的思维激荡。对此我深有体会,——我曾与一位导师共同挑战另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智力项目,当时至少在心理层面有类似的体验。那个项目也试图填补我们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巨大空白——我们当时想通过所谓的「整合信息论」来建立一门意识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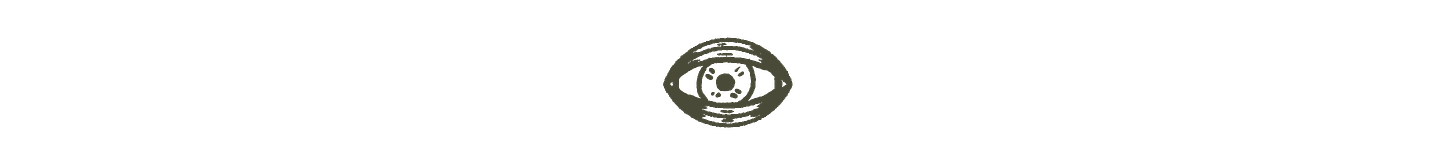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历史上关于年轻天才们的日常作息,留下来的细节寥寥无几。很多时候,唯一的详细信息来源就是天才本人的自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中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启示。首先,并不存在什么从一门学科到另一门学科的「标准最佳学习路径」,也没有引入某个特定学科的「最佳时机」,更找不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教学方案。以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为例——他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虽同享父亲的贵族式辅导(其父身为税务官员,家境优渥、学识渊博,对教育理论也颇有研究),但培养规划和科目顺序大相径庭。这位后来的伟大数学家直到十多岁才接触数学,此前其父刻意将数学书籍锁在家中别处,以免儿子过早分心。语言学习同样被推迟到12岁;在此之前,他父亲先讲授通用的语法规则,习得基本原理后才学习具体语言。(根据《布莱士·帕斯卡:心灵的理由》(Blaise Pascal: Reasons of the Heart),帕斯卡的父亲也辅导了他的女儿杰奎琳·帕斯卡(Jacqueline Pascal),把她培养成一位文学神童。)
因此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既不是辅导课程的时间安排,甚至也不是所授科目选择。纵观历史上那些最杰出且详实记载的案例,关键要素在于:(a) 孩子与热衷智力探索的成年人进行一对一深度交流的总时长;(b) 有一位强有力的主导者,以培养卓越人才为明确目标,从宏观层面把控教育方向(比如密尔的父亲、罗素的祖母、汉密尔顿的导师诺克斯,以及现代例子如数学家陶哲轩的父母);(c) 充足的自由时间,即每天的辅导时间比传统学校少;(d) 教学要避免死记硬背和应试导向,转而鼓励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思考,鼓励讨论、写作、辩论,或者仅仅是一起梳理基础;(e) 在这些活动中,最好让学生自己主导(比如写文章、作诗、推导证明);(f) 导师或整个家庭必须对智力生活抱有异乎寻常的认真态度;(g) 天才往往很早就显露出专业化倾向,且常常就是他们日后大放异彩的领域(比如汉密尔顿童年处理物流的经验,让他成了华盛顿麾下理想的幕僚长);(g) 在某个阶段(通常很早),辅导会转变为学徒模式,采用项目合作的形式,比如一起完成论文、专著或书籍;(h) 最后一步通常是在刚成年时,拜入另一位正值巅峰的天才门下(如密尔师从边沁父子等早期功利主义者,罗素师从怀特海,汉密尔顿追随华盛顿)。自此,他们便开启了自己的征程。在更早的年代,这些天才功成名就后,自己往往也会成为导师,仿佛生命走完一个轮回,又回到了起点(例如,曾受教于当时名噪一时的科学家的惠更斯,后来又辅导了莱布尼茨)。
那么,今天的罗素们、密尔们,甚至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或许能得到父母的精心呵护,比如陶哲轩:被留在父母身边,就读一所压力不大的本地大学,遵循一套与标准学术晋升路径迥异的、量身定制的培养方案。但在更多情况下,这些潜在的天才很可能只会被塞进那个擅长打造「平均水平」、却不利于培养顶尖人才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结果会如何?
我想,他们本人的话最有说服力。听听伯特兰·罗素怎么说他与考试的关系:
钻研考试技巧的过程,让我误以为数学就是些投机取巧的解题捷径,就像在玩填字游戏。等……我考完最后一场数学考试,我发誓再也不碰数学,还把我所有的数学书都卖了。
再看爱因斯坦——这位群星璀璨的天才殿堂中最耀眼的存在——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后不久写下的文字:
(考试带来的)强制感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抑制作用,以至于在我通过期末考试后,整整一年里,一想到任何科学问题就犯恶心。
本文是「贵族式辅导」系列的第三部分。本系列开篇为《为什么西方不再出产爱因斯坦》(第一部分),随后是《对贵族式辅导重要性的几点反驳》(第二部分)。感谢 Escaping Flatland 博客的 Henrik Karlsson 为第三部分提供的资料支持。